時間:2023-03-06 16:06:11
引言:易發(fā)表網(wǎng)憑借豐富的文秘實(shí)踐,為您精心挑選了九篇關(guān)于中國夢的詩歌范例。如需獲取更多原創(chuàng)內(nèi)容,可隨時聯(lián)系我們的客服老師。

2012年11月,在參觀《復(fù)興之路》展覽時首次提出:“實(shí)現(xiàn)中華民族的偉大復(fù)興”是新的“中國夢”。今年5月4日,在中國空間技術(shù)研究院同各界優(yōu)秀青年代表座談并發(fā)表重要講話中再次闡釋了青年與中國夢。總書記講話滿懷深情,寓意深遠(yuǎn),具有很強(qiáng)的思想性、指導(dǎo)性和針對性,為廣大青年健康成長成才進(jìn)一步指明了方向。
青年最富有朝氣、最富有夢想,青年興則國家興,青年強(qiáng)則國家強(qiáng)。廣大青年要堅(jiān)定理想信念,練就過硬本領(lǐng),勇于創(chuàng)新創(chuàng)造,矢志艱苦奮斗,錘煉高尚品格,在實(shí)現(xiàn)中國夢的生動實(shí)踐中放飛青想,在為人民利益的不懈奮斗中書寫人生華章。指出,歷史和現(xiàn)實(shí)都告訴我們,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擔(dān)當(dāng),國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實(shí)現(xiàn)我們的發(fā)展目標(biāo)就有源源不斷的強(qiáng)大力量。
我們在學(xué)習(xí)的“五四”重要講話時,要努力做到“四個深刻理解”,即深刻理解當(dāng)代青年在實(shí)現(xiàn)中國夢偉大進(jìn)程中肩負(fù)的歷史使命,引導(dǎo)青年不斷增強(qiáng)為實(shí)現(xiàn)中國夢而奮斗的責(zé)任感、使命感;深刻理解為實(shí)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fù)興的中國夢而奮斗是中國青年運(yùn)動的時代主題,勇敢地接過前人的接力棒,肩負(fù)起屬于當(dāng)代青年的光榮使命;深刻理解實(shí)現(xiàn)中國夢是青年成長成才的最好舞臺,自覺把個人追求和奮斗融入這一進(jìn)程,共同支撐、共同見證、共同享有偉大的中國夢;深刻理解當(dāng)代青年是實(shí)現(xiàn)中國夢的一支強(qiáng)大的有生力量,青年樹立共同理想,中國夢的實(shí)現(xiàn)就會擁有生生不息的力量。
當(dāng)代中國青年認(rèn)真領(lǐng)會和實(shí)踐重要講話對青年提出的要求,明確成長發(fā)展、建功立業(yè)的正確道路,還要努力做到“五個深刻認(rèn)識”。即深刻認(rèn)識堅(jiān)定理想信念是青年成長成才的核心靈魂,增強(qiáng)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堅(jiān)定跟黨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人生信念。深刻認(rèn)識練就過硬本領(lǐng)是青年成長成才的牢固根基,不斷提高素質(zhì)、增強(qiáng)本領(lǐng),努力成為可堪大用、能擔(dān)重任的棟梁之材。深刻認(rèn)識勇于創(chuàng)新創(chuàng)造是青年成長成才的時代要求,在積極投身建設(shè)創(chuàng)新型國家、實(shí)施創(chuàng)新驅(qū)動發(fā)展戰(zhàn)略的實(shí)踐中體現(xiàn)價值。深刻認(rèn)識矢志艱苦奮斗是青年成長成才的精神支柱,用頑強(qiáng)的意志和勤勞的雙手攻堅(jiān)克難、成就夢想,不斷開辟事業(yè)發(fā)展的新天地。深刻認(rèn)識錘煉高尚品格是青年成長成才的立身之本,加強(qiáng)思想道德修養(yǎng),保持積極的人生態(tài)度,踐行先進(jìn)的道德風(fēng)尚,以實(shí)際行動促進(jìn)社會進(jìn)步。
實(shí)現(xiàn)中國夢,青春勇?lián)?dāng)。當(dāng)代中國青年要實(shí)現(xiàn)自己的人生理想必須將中國夢融入個人發(fā)展目標(biāo),而中國夢的實(shí)現(xiàn)也需要敢夢、筑夢、圓夢的有志青年來完成。我們要銘記歷史賦予青年的責(zé)任,胸懷民族復(fù)興的夢想,堅(jiān)持真理,砥礪奮進(jìn),為實(shí)現(xiàn)偉大的中國夢貢獻(xiàn)青春、智慧和力量,在實(shí)現(xiàn)中國夢的偉大實(shí)踐中去書寫人生最華麗的篇章!
1、 關(guān)于文學(xué)園地:是冬天爐中的一團(tuán)炭火,可以讓人取暖;是世俗世界的一縷清風(fēng),可以給人撫慰。
2、 關(guān)于文學(xué)獎項(xiàng):是一種人文激賞,是一種人生喝彩;為在文學(xué)之途寂寞趕路的一群人點(diǎn)亮了一盞燈。善莫大焉,功莫大焉。
隨想之二:激賞一個散文家――朱小軍――有魏晉筆記小說簡約之風(fēng),得明清散文小品輕淡之范。
1、 他是一個文學(xué)學(xué)養(yǎng)深厚的人。他讀書可以讀到淚眼婆娑,他作文可以讓人咀嚼再三。他以五十多年人生閱讀之積累,爾后始于表達(dá),所謂厚積薄發(fā)是也,所謂居高聲自遠(yuǎn)是也。其看似散漫、輕淡、簡約而為的文字,甫一問世便成為了一個事件,成為了一個現(xiàn)象。現(xiàn)在,在東風(fēng)文學(xué)圈內(nèi),大家見面常常問一句:“你讀朱小軍了嗎?”
2、 朱小軍所寫之人之事,是一個時代一個群體的人文記憶,是一個時代一個企業(yè)的精神涵養(yǎng)。它是東風(fēng)人的口述歷史,是東風(fēng)公司的人文《史記》,全是紀(jì)實(shí),因此,它是歷史的;同時,它又是文學(xué)的,所有文字,寫人記事,你盡可以當(dāng)作志人之類的筆記小說讀,平和而不平靜,簡約而不簡單,在文字之外自有大波浪,大天地――他直抵人心,觸動人,溫暖人,撫慰人。
3、 我以為,朱小軍文字的路數(shù)是純粹中國的,有魏晉筆記小說簡約之風(fēng),得明清散文小品輕淡之范。是根植于中國文化沃土的,是在中國文人學(xué)士圈里一直流傳的文風(fēng),文脈。
4、 納博科夫?yàn)槭廊肆粝铝嘶貞涗洝墩f吧,記憶》,希望朱小軍的系列文章只是熱身,是開始 ,希望他接下來繼續(xù)說吧,寫吧。
隨想之三:推薦一個詩人――蔡崢嶸――詩味與詩感共生,優(yōu)美與優(yōu)雅同在。
1、 蔡崢嶸的詩合符我個人閱讀詩歌的興趣取向,即所謂詩歌“三昧”:有味道,可誦讀,深究一番讀得懂。故推薦之。
2、 蔡崢嶸的詩是干凈的詩,是明麗的詩,像山泉水,像純凈水,像礦泉水,幾乎就沒有什么雜質(zhì)在。
3、 蔡崢嶸的詩是有詩味的詩,是輕靈的詩,是輕盈的詩,也是起伏飄逸的詩。好比酒出自糧食谷物,它是水鄉(xiāng)清酒,是房縣黃酒,是紹興花雕,綿香而又純粹,清冽而不濃烈――我們撫摸打在日子上的補(bǔ)丁/抹去生活的鹽分/繼續(xù)說愛/說童年的故鄉(xiāng)/說著說著春風(fēng)就擠進(jìn)門縫。這樣的詩,品嘗一口,滿嘴生津。
4、 蔡崢嶸的詩是有詩感的詩,是生動的詩,是有情趣的詩――當(dāng)一只蝴蝶俯沖藍(lán)/當(dāng)藍(lán)分泌藍(lán)/我想走向比藍(lán)更藍(lán)的地方。――我以為,詩的感覺,或者說生動,是詩歌、詩人高下之別的主要指標(biāo),是衡量詩歌、詩人是否優(yōu)秀的KPI,其他都可以是從屬和其次。
5、 有詩感的詩,有詩味的詩,是可以透著一份優(yōu)美與優(yōu)雅的,就仿佛京劇里的梅蘭芳,小說里的沈從文,歌曲里的王洛賓。
6、 李白是熱鬧的,浪漫的,豐富的,王維是平和的,安靜的,明亮的,他們并不見得十分深刻,但他們絕對優(yōu)秀與偉大。蔡崢嶸,愿照此在詩歌之路走下去,且一路走好,寫出更多優(yōu)美與優(yōu)雅的詩!
隨想之四:致敬一個小說家――傅祥友――在文學(xué)園地,他是一個堅(jiān)持者和堅(jiān)守者,他是一個可以把生命托付給文學(xué)的人,他是東風(fēng)人文領(lǐng)域里一道最美麗風(fēng)景線。
1、 在文學(xué)之途,雖踽踽前行,但總是在行,而且沉浸其中,從不回頭。這就是傅祥友。其人也義氣,其行也正氣,其文也生氣,其悟也真氣。
2、 普天之下,皆可冷嘲;率土之濱,無不熱諷。時而還間雜一點(diǎn)調(diào)侃,這是祥友能耐所在,更是他風(fēng)格使然。是的,祥友積十年之訓(xùn)練與修煉,還真有了那么一點(diǎn)契科夫的味道。其語言也是這樣的,不僅增添了一點(diǎn)韻味,而且生出了一些張力,最終具有了內(nèi)容性與文化性。是明顯的成績與進(jìn)步,是需要保持與發(fā)揚(yáng)的。
3、 感受于文學(xué)之美妙,體味于創(chuàng)作之神圣,祥友敢與青燈相伴,可以生命相許。當(dāng)今之世,如斯之人,能有幾何?如此精神,這般狀態(tài),當(dāng)贏得全體起立鼓掌致敬。
4、如果在明處省一點(diǎn)力,比如說能夠從語言中出得來;如果在暗處多用點(diǎn)勁,比如講對故事多一分經(jīng)營,那么,在現(xiàn)有格局之上還將增長幾分境界,祥友便會化蛹為蝶,一飛沖天了。
隨想之五:賞析一個作者群――漸顯個性,漸成風(fēng)格,漸成風(fēng)氣。
1、 周中:他是今天東風(fēng)詩歌繞不過去的一個人。盡管其見諸于報刊雜志的作品并不十分多,但據(jù)說其寫作量是驚人的。縱觀周中詩歌,其文也華麗,其采也艷麗,其氣也壯麗,其勢也雄麗。先說其文、其采,周中的詩是美文中的三島由紀(jì)夫,華美而不鋪陳;是美食中的東坡肘子,肥美而不膩歪;是美人中的楊貴妃,豐腴而不肥胖。再說其氣、其勢,周中的詩是眉飛色舞的,是高聲闊論的,是恣睢的,是排山倒海的,聞其聲,是高音中的多明戈;品其味,是美酒中的二鍋頭;辨其色,是百花中的紅牡丹;觀其勢,是河流中的瀾滄江。此等文采,這般氣勢,其底蘊(yùn)與涵養(yǎng)只能是中國文化,是中國詩詞。
2、王征珂:有一種記憶是童年,有一種意象是童趣,有一種表達(dá)是童謠。王征珂是幸福的,在紛繁熙攘的塵世,其精神總是生活在童話里,并且始終做著一個清醇歌者的夢,二十多年了都不醒過來。他又是敏感、可愛的,像鄰家那個缺了門牙捂嘴賣萌的小妹崽,其喜怒哀樂全是童謠的,也全是詩歌的。但是,其聲音又不全是稚嫩,發(fā)出的又不全是嗲聲,其人其文也絕不一覽無余,絕不清澈見底。因此,王征珂的詩往往是初春遠(yuǎn)處的湖面,是初夏早晨的原野,總有一種薄霧在繚繞,也總有一種水汽在升騰,所呈現(xiàn)出的是一種萌態(tài)美,氤氳美,朦朧美,迷離美。
3、趙明的《江上人家》――靈性初現(xiàn),像早春枝頭,讓人眼前一亮;李俊玲的《活著》――人性燭照,像爐膛炭火,讓人心頭一熱;姚天賜的《夢長安》――心性勃發(fā),像天馬行空,讓人超然物外;尹琦的《走在城市心中》――天性點(diǎn)化,像酷暑冰啤,讓人全身通泰;陳宏的《大年夜》――率性而為,像冰糖葫蘆,讓人酸酸甜甜。
古詩詞作為中國文化的重要載體,表現(xiàn)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所特有的審美和思維方式,同時證明了中國文化具有深刻的內(nèi)涵。在表現(xiàn)手法上,詩的內(nèi)涵通過中國文化表現(xiàn)出來,這樣,就拓展了空間,增添了韻味;同時也體現(xiàn)出古詩詞的精神,超越了一些表層因素,如詩詞的音韻、格律、措辭等。
在翻譯古詩詞時,通常情況下,都喜歡用“歸化”或“異化”來傳遞詩詞的文化意象。歸化(domestication)指在翻譯中,最大程度淡化原詩詞的陌生感,使原文變得流暢、透明。這種方法是使古詩詞中的語言盡可能地反映讀者接受的觀點(diǎn),從而達(dá)到古詩詞文化與讀者所熟悉文化之間的一種對等。異化(foreignization)指翻譯者在翻譯原文時,背離其主流文化,盡可能保留原文的文化,使翻譯和原文之間具有一定的差異;而且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打破原來的翻譯原則,盡量保留原詩詞的本色特征。即在翻譯中保留原詩詞文化特點(diǎn),以豐富譯文和原詩詞的語言表達(dá)。
古今中外,在翻譯《紅樓夢》詩詞的時候,楊氏夫婦和霍克斯的譯本是比較權(quán)威的,他們是楊氏夫婦的“A Dream of RedMansion”和大衛(wèi)霍克斯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因?yàn)楦髯缘纳畋尘安煌苑g的意境不同,都對中國古詩詞文化運(yùn)用了完全不一樣的翻譯。中國的楊氏夫婦用的是異化法。他的目的是把中國的特色和主流文化介紹給西方國家。而英國的霍克斯采用歸化法,他是想盡可能使讀者通過閱讀詩詞來接受中國詩詞的特點(diǎn)。
《紅樓夢》中的詩歌特別多,在這里拿出幾個例子來進(jìn)行比較分析。《紅樓夢》中元妃歸省,作為弟弟的賈寶玉應(yīng)元妃而做的《有鳳來儀》“竿竿青欲滴,個個綠生涼”。楊氏夫婦和霍克斯的譯法完全不同:楊譯為“So green each stem they seem to drip”;而霍譯為“Each graceful land lets fall a dewy tear”。在原文詩詞里,“青欲滴”是漢義的“青翠欲滴”。在翻譯時,楊氏夫婦充分利用了中國的文化特點(diǎn),使讀者一看就知道意思;而霍克斯則因?yàn)閷ξ幕恼`解,翻譯成露珠從竹子上滑落,這樣,就使看的人不知所云。還有一句“莫搖清碎影,好夢晝初長”,楊氏夫婦譯為“Letnon disturb these chequered shades,That sweetly she may dream till daylight fades”。用“Sweetlv”是擬人化的把竹子翻譯出來,完全適合原詩中的情節(jié)。而霍譯為:“Let none the checkered shade withviolence rude,Disturbing on slum-beer’s dream intrude!”霍克斯用了“violence”和“intrude”,這兩個詞和原文意思非常押韻,但用在這里不恰當(dāng),語氣不夠委婉。
春去夏來黛玉傷春感花悲己身做了一首《葬花詞》其中中“花謝花飛花滿天,紅消香斷有誰憐?”楊氏夫婦翻譯成:“Asblossoms fade and ny 8cross the sky,Who pities the faded red,the scentthat has been?”而霍克斯則譯為:“The blossoms fade and falling fillthe air,fragrance and bright hues bereft and bare”在這兩句翻譯中,霍克斯的翻譯工整押韻、優(yōu)美簡練,非常漂亮,然而卻沒有原文的“有誰冷”的意思,和原詩詞要表達(dá)的就不同了。
以上是通過對比、比較楊憲譯和霍克斯兩種詩歌翻譯意象傳遞的現(xiàn)象,從而知道楊氏夫婦和霍克斯在翻譯時所采用的翻譯策略有著很大的區(qū)別。楊氏夫婦運(yùn)用了異化的翻譯手法,在翻譯詩詞時,盡量忠實(shí)原詩詞形象,同時還采用了加注、增詞和直譯的方法來保留中國古代文化的一種獨(dú)特意象,使讀者從譯文中了解中國古文化;而霍克斯采用的是歸化的方法,翻譯時工整押韻,盡量地想表達(dá)出翻譯的完美形式,這樣,在很大程度上就會舍棄原文中的文化意象,雖然可讀性很強(qiáng),但卻沒有保留原詩詞的文化特征和詩詞意蘊(yùn)。因此,兩者在翻譯時各有千秋,要根據(jù)語境的不同來做適當(dāng)?shù)姆g,不能一味地運(yùn)用異化和歸化。
一、 迷幻敘事風(fēng)格的建構(gòu)
(一)戲劇性弱化
戲劇性源自戲劇藝術(shù),但被引征自電影藝術(shù)中,日本學(xué)者竹登志夫?qū)ζ涠x為:“所謂戲劇性,即是包含在人們?nèi)粘I钪械哪承┍举|(zhì)矛盾,這種同人和他者的潛在對立關(guān)系,是一個隨同時間的流逝在現(xiàn)實(shí)人生中逐漸表面化、在強(qiáng)烈的緊張感中偏向一方,從而達(dá)到解決矛盾的一連串過程。”[1]從敘事而言,影片敘事的戲劇性被弱化,如老醫(yī)生緬懷兒子燒紙錢時,僅以“平常天”這一回答掩飾了所有的懷念,并不著力刻畫老年喪子的悲傷,弱化了事件的戲劇性,但卻強(qiáng)化了隱忍不發(fā)的情感。陳升尋找陳英的橋段更是略去了戲劇性的復(fù)仇情節(jié),而以帶著戾氣的詩歌與空鏡頭轉(zhuǎn)換至新時空。而隨后陳升尋找衛(wèi)衛(wèi)的過程亦是如此,在花和尚不愿意歸還衛(wèi)衛(wèi)時,陳升寬以期限,略帶憐憫地留下了紐扣,影片中對于事件的處理均刻意弱化戲劇性,從而導(dǎo)致敘事的不流暢,布爾的情緒理論暗示意識或認(rèn)知限制著情緒。“當(dāng)個體在連續(xù)的認(rèn)知過程中,他的意識中可能就不存在情緒。反之,如果個體處于斷裂的認(rèn)知過程,那么他就會體驗(yàn)到情緒。”[2]在心理學(xué)中,情緒是包含著情感的。在認(rèn)知中斷時情緒會慢慢的流淌開來,影片中為了實(shí)現(xiàn)個體的情感表達(dá),以弱化情節(jié)戲劇性的方式實(shí)現(xiàn)隱而不宣的所指指向性,讓觀眾在認(rèn)知中斷的裂縫中靜靜體驗(yàn)出作品濃烈的情感和深邃的詩意化美境。
(二)碎片化敘事
從影像敘事的特點(diǎn)來說,作品依托網(wǎng)狀的碎片化敘事充分探索了影像敘事的多義性與含糊性。從敘事結(jié)構(gòu)來說,影片以過去、現(xiàn)在、未來編織成一張時空交錯之網(wǎng)。從敘事方式來說,散點(diǎn)式的事件則散落在這張網(wǎng)的每個角落,且每個事件與前后事件之間缺乏直接的邏輯聯(lián)系。從敘事線索來說,屬于并發(fā)性多線索式,現(xiàn)實(shí)中的陳升醫(yī)治病人、與老醫(yī)生的對話、照顧衛(wèi)衛(wèi)、尋找老歪、尋找衛(wèi)衛(wèi),而在這一隱約可見的現(xiàn)實(shí)敘事線索中,拼綴上陳升的夢境和過往經(jīng)歷的回憶片段。影片亦穿插了一些齊頭并進(jìn)的輔敘事線索,如老醫(yī)生光蓮和蘆笙藝人林愛人的浪漫過往,酒鬼司機(jī)撞死年輕人的故事,花和尚兒子被殺事件、因?yàn)槟赣H遺產(chǎn)而心生齷齪的兄弟二人,青年衛(wèi)衛(wèi)對洋洋的戀慕也正是在這張情義滿滿卻錯綜復(fù)雜的時空之網(wǎng)里,陳升面對了過往,了然于未來,安然于當(dāng)下。
(三)超現(xiàn)實(shí)主義表述
1. 荒誕魔幻的意象
影片中使用了大量不合邏輯的荒誕意象,如用來取暖的手電筒、破舊的屋外懸掛的舞燈、倒轉(zhuǎn)的指針、爛醉撒瘋的酒鬼、撓野人癢癢的長棒,影像中的很多意象都與常規(guī)經(jīng)驗(yàn)中的認(rèn)知截然相悖離,因而產(chǎn)生脫離現(xiàn)實(shí)情境的荒誕感。而語言所建構(gòu)的敘事因言語的不確定性及多義性更是強(qiáng)化了意象與現(xiàn)實(shí)的間離感,如陳升描述與妻子相處的情境時,言及二人幸福地生活在一間帶山瀑的小屋里,但由于水聲太大,沒法說話只能跳舞,以荒誕的意象來襯托真摯的情感。花和尚及老歪商量帶走衛(wèi)衛(wèi)的場景亦是充滿了魔幻的意味,在衛(wèi)衛(wèi)答應(yīng)隨同花和尚前往鎮(zhèn)遠(yuǎn)之后,鏡頭隨著聲音移轉(zhuǎn)至窗邊隆隆前行的火車上,創(chuàng)造出一幅超現(xiàn)實(shí)的魔幻畫面,也隱喻了花和尚與衛(wèi)衛(wèi)的離開,影片通過系列具有象征意味的荒誕元素與魔幻的場景設(shè)計建構(gòu)出亦真亦幻的迷幻式本土化詩意空間。
2. 意識流般的表述
影片中不論是老醫(yī)生關(guān)于故人及兒子的夢境,還是陳升關(guān)于母親的繡花鞋及蘆笙環(huán)繞的夢境,亦或是花和尚被砍手指兒子的夢境,都深深牽引著陳升去解開內(nèi)心不能平息的波瀾。在老醫(yī)生的囑托下,自我的深思里,更是在魂繞夢牽的夢境的指引下,陳升背起行囊去釋夢人,及至蕩麥所遭遇的一切,更像是隨著陳升的意識流牽引而不斷遇見自己家人的過程,如遇見青年衛(wèi)衛(wèi),在洋洋縫紉店遇見年輕時的張夕,追隨洋洋坐船,朗誦導(dǎo)游詞,莫名其妙地返回,買風(fēng)箏,洗頭發(fā),事件與事件之間并無邏輯關(guān)聯(lián),更像是以思緒飄蕩而至的偶遇。這些隨心所見的人或場景更多是陳升的內(nèi)心世界的真實(shí)關(guān)照,這一波瀾起伏的心理狀態(tài)描繪與詩意所需的飄忽不定及變形極為契合,也合力作用為一次超越現(xiàn)實(shí)的詩意化心靈救贖之旅。
二、 詩意化風(fēng)格營造
(一)詩歌:詩意化旁白的抒情
“言語具有解釋概念的力量和追憶過去、預(yù)測未來的能力。”[3]使用語言更能夠建構(gòu)出跨越過去、現(xiàn)在、未來的時空之橋,調(diào)度人們的想象與創(chuàng)造能力,使得人們在思維空間里自由來去,從而借助語言藝術(shù)的魔術(shù)及紀(jì)實(shí)的畫面盡情表情達(dá)意。言語的抽象及變形使得它們更易于表述情感及精神之類的信息,這一獨(dú)特的優(yōu)勢使得其在詩意化風(fēng)格的營造上極具優(yōu)勢。影片共使用了八首現(xiàn)代詩來表述不同情境下主人公的情感與狀態(tài),影片在大量的長鏡頭里不時插入詩歌,以消解長鏡頭可能帶來的單調(diào)與乏味,最終,讓人不再在意鏡頭里的意象,轉(zhuǎn)而浸在詩歌構(gòu)建的情境里,如陳升出獄時以:“玫瑰吸收光芒,大地按捺清香,為了尋找你,我搬進(jìn)鳥的眼睛,經(jīng)常盯著路過的風(fēng)。”表達(dá)了對于美好生命的向往及對于家人愛的期待。而至夢境疲憊醒來的陳升枯坐在沙發(fā)里,以詩歌“你攝取我的靈魂,沒有了剃刀就封鎖語言,沒有心臟卻活了九年”表述了失去母親和愛人9年間的孤獨(dú)和失落。及至蕩麥之行結(jié)束之時,成年衛(wèi)衛(wèi)載陳升去河邊候船時行駛在盤旋的山路間,以詩歌“一定有人離開了會回來,騰空的竹籃裝滿愛”表達(dá)了陳升對于未能對母親盡孝道情感的釋懷。以長短句式的現(xiàn)代詩歌表述情感的段落,毋庸置疑地直接嫁接了中國文學(xué)中詩詞的表意方式,因而影片中人物的情感表述更多源自具有本體化審美言語的抒情化表達(dá),也即影像段落的詩意更多與詩歌的抒情性直接勾連,同時,洋溢著黔東南風(fēng)情畫面則淪為輔助角色,與詩意化旁白共同建構(gòu)出本土化詩意。
(二)聲畫結(jié)合:勾連詩性藝術(shù)空間
影像通過聲畫結(jié)合實(shí)現(xiàn)不同時空的勾連,長鏡頭在陳升尋找陳英復(fù)仇這一段落的處理中有極強(qiáng)的藝術(shù)假定性,陳升尋找老歪質(zhì)疑墓碑為何未加自己名字發(fā)生爭執(zhí)的空間與陳升為花和尚兒子復(fù)仇的空間在導(dǎo)演的精心組織下被安置在一起,并通過畫外音交代了復(fù)仇事件,在爭執(zhí)聲弱化時,陳升那濃厚黔南口音的詩歌朗誦含蓄而概括地表達(dá)了事情的發(fā)展,鏡頭則慢慢轉(zhuǎn)向爭執(zhí)的群體旁的紅色桌子、雨水以及倒下的玻璃杯,繼而以安靜的長鏡頭靜靜地凝視著不斷滴落的雨滴,當(dāng)陳升夾雜著黔南口音的詩歌朗誦結(jié)束時,畫外音再次傳來,鏡頭跟隨著畫外音向左轉(zhuǎn)去,轉(zhuǎn)向正在爭執(zhí)的陳升與老歪,這一段落通過詩意化的旁白以及空鏡頭下的室內(nèi)物件,勾連了現(xiàn)在、過去、現(xiàn)在的空間,也即以聲畫結(jié)合的方式建構(gòu)了不同時態(tài)下完整的詩性藝術(shù)空間。
(三)長鏡頭:現(xiàn)實(shí)空間的多義與模糊
影片最為典型的是長鏡頭的使用,以長鏡頭保有影像本身“對外部現(xiàn)實(shí)先天的近親性”[4]。這一拍攝方式與巴贊的觀點(diǎn)不謀而合。“長鏡頭既是一種攝影技法,更是一種創(chuàng)作理念和美學(xué)風(fēng)格。它能保持電影時間與電影空間的統(tǒng)一性和完整性。”[5]保有影像時空的曖昧與多義性。影片中以大量行駛于盤山公路上的主觀式長鏡頭攜裹著情感充沛的詩歌激蕩著我們內(nèi)心隱秘的情愫,關(guān)于孤獨(dú)、意義、情感、記憶、尋找、眷念、愛,這些富有內(nèi)涵的主題躍動在方言氣息濃厚的本土化詩歌里,也在霧氣氤氳的盤山旅途中發(fā)酵,以長鏡頭這種貼近真實(shí)時空的記錄方式來建構(gòu)內(nèi)心世界的藝術(shù)時空,并以冷靜的長鏡頭刺穿浮動的表象,塑造出生成與變化的綿延之美,折射出透徹而又無奈的現(xiàn)實(shí),這是一種極具創(chuàng)造力的藝術(shù)化表現(xiàn)方式。
影片以42分鐘的長鏡頭模糊了現(xiàn)實(shí)與虛幻的界限,創(chuàng)造了時空的多義性與模糊感,在陳升坐在車尾望向窗外的迷糊眼神里,也在陳升行駛于煙霧氤氳的盤山公路的獨(dú)白里,影片以搖擺不定的長鏡頭化作德勒茲所言及的時間“切片”。與交融于一起的過去、現(xiàn)在、未來三個時間維度有著某種意義上的契合。蕩麥?zhǔn)且幻嬲凵渲鵁o間隙時空的哈哈鏡,在蕩麥坡上坡下忽高忽低起伏的鏡面里,蕩漾著人物內(nèi)心起伏不已的情緒。在這里,陳升在唱給逝去妻子的《小茉莉》里放下遺憾,在安靜凝望衛(wèi)衛(wèi)的望遠(yuǎn)鏡里,充盈著滿滿的愛意。從詩意的營造來說,詩意需要一個獨(dú)立的、不同于尋常的表現(xiàn)方式,這一方式要能夠迫使原本含義清晰的語詞更新選擇和組合能指的意義,以構(gòu)成詩意,這種方式被利科形象地描述為“虛擬”和“懸置”。[6]影片恰恰以紀(jì)實(shí)風(fēng)格的長鏡頭影像與意識流般的敘述建構(gòu)了“虛擬”和“懸置”的邊界模糊的影像空間。在蕩麥,陳升實(shí)現(xiàn)了自我靈魂的救贖,遇見了肖似妻子的理發(fā)店女孩,遇見了與侄子同名的青年衛(wèi)衛(wèi),遇見了自己,在搖擺不定的長鏡頭創(chuàng)造出的夢境般的褶皺,觀者如同遁入波瀾洶涌的夢境。在蕩麥,老陳在《金剛經(jīng)》言及的“過去心不可得,現(xiàn)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里尋得本心――那就是當(dāng)下。他如同幽靈游蕩,尋找,停留,行走,與遇見的每個過去瞬間悉心交流,彌補(bǔ)遺憾;也與遇見的未來某個時刻而傾盡愛意,不留遺憾。影像中長鏡頭安靜凝視里大量的信息“空置”有些類似于伊蓮?布萊斯基所言及的詩歌中隱秘的線,它懸置在某個地方,每一次都需要重新捕捉。”[7]也類似于中國畫“留白”不能簡單地理解為“虛無”,而是一種“藏境”的手法,是一種含蓄的藝術(shù)表達(dá)方式,意圖營造出一種深邃的意境。[8]影片中為了實(shí)現(xiàn)特定的情感表達(dá),以藝術(shù)化的信息“空置”實(shí)現(xiàn)隱而不宣、懸而不置的所指指向性,讓觀眾在認(rèn)知中斷的裂縫中靜靜體驗(yàn)出作品濃烈的情感和深邃的詩意化美境。
三、 意境與中國式詩意
影片借助詩歌朗誦的旁白與長鏡頭下情感含蓄的本土化生活畫卷結(jié)合,完美地闡釋了塔爾科夫斯基提及的“電影的詩意”,這是“讓思想和情感主宰劇情發(fā)展的、接近生命本身的、最真實(shí)的、詩意的藝術(shù)形式。”[9]無論是影像藝術(shù)的詩學(xué),還是詩意的詩學(xué),最終都上升至了一個較為統(tǒng)一的狀態(tài),即可以感受,卻難以言說的境界。也即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論述的“意境”。勾連至電影的詩意表達(dá),亦需要通過影像建構(gòu)出“鏡已盡,但境未盡”的意猶未盡之境。我們在長鏡頭的安靜凝視里,感受到老醫(yī)生對兒子、花和尚對兒子、陳升對母親無窮無盡的懷念;體會到陳升與妻子、老醫(yī)生與故人、甚至青年衛(wèi)衛(wèi)與洋洋那道不盡的眷念;無論是取暖的手電筒,還是化成追逐海豚光影的手電筒,影片都以以含蓄而隱忍的方式展現(xiàn)了意猶未盡的情感。而陳升對于衛(wèi)衛(wèi)的呵護(hù)亦是持久而穩(wěn)固的,以理解花和尚的孤獨(dú)為開始,以堅(jiān)持接回衛(wèi)衛(wèi)的陪伴為終始。影片至始至終未著“情”與“愛”字,但卻在平靜的守候與追憶間化出超越話語的萬千思緒,確實(shí)“相似的所有的懷念隱藏在相似的日子里”。在長鏡頭所掠過的一幅幅黔南霧氣氤氳的生活畫卷里,在山、水、人、物的情景交融中,展現(xiàn)出韻味無窮的美感特征,呈現(xiàn)出生命律動的本質(zhì)特征,凝聚了對于生命意義的思考。影片最終在關(guān)于生命最重要的陪伴里尋找到了詩意的棲居之所,誠如詩歌中言及的當(dāng)內(nèi)心充盈著愛,“這對望的方式,接近古人,接近星空”。
關(guān)鍵詞: 闡釋學(xué) 譯者主體性 林黛玉詩歌 《題帕三絕句》 英譯本對比
譯者是翻譯過程中最活躍的因素,然而傳統(tǒng)的翻譯理論研究卻忽視了譯者這翻譯活動中最積極的因素,其作用并未得到應(yīng)有的肯定。兩千多年來,譯者被冠以多種稱號,如“媒婆”、“隱形人”、“舌人”、“施暴者”、“翻譯機(jī)器”、“文化搬運(yùn)工”、“二主一仆”中的仆人、“戴著鐐銬的舞者”等,這體現(xiàn)了對翻譯,特別是譯者價值的否定。作為主體的譯者不但沒有引起廣泛的關(guān)注,相反譯者在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上一直處于邊緣地位。二十世紀(jì)七十年代以來,西方譯論的“文化轉(zhuǎn)向”為我們開辟了譯學(xué)研究的新視角。關(guān)于翻譯主體性的研究受到西方理論界的廣泛關(guān)注,Susan Bassinet的《文化,構(gòu)建,翻譯》是這股潮流的代表,自此翻譯研究開始從單純的語言學(xué)角度進(jìn)入到文化歷史的宏觀大環(huán)境中。隨著對翻譯理論中闡釋學(xué)研究的深入,人們逐漸加深了對翻譯活動本質(zhì)的認(rèn)識和對譯者主體性的肯定。
一、闡釋學(xué)與譯者主體性
闡釋學(xué)(Hermeneutics)是二十世紀(jì)六十年代廣泛流傳于西方的一種哲學(xué)和文化思潮,它是關(guān)于探究意義的理解和解釋的理論,已成為當(dāng)代最具生命力的哲學(xué)思潮之一,其理論影響幾乎滲透到所有的人文學(xué)科,甚至是自然科學(xué),并以海德格爾和伽達(dá)默爾為代表。伽達(dá)默爾秉承海德格爾的本體論轉(zhuǎn)變,把闡釋學(xué)進(jìn)一步發(fā)展為系統(tǒng)的現(xiàn)代哲學(xué)闡釋學(xué),將其推向興盛。伽達(dá)默爾說:“一切翻譯已經(jīng)是闡釋,我們甚至可以說,翻譯始終是解釋的過程。”闡釋學(xué)起初的研究方向主要是針對藝術(shù)作品的理解和解釋,而翻譯的實(shí)質(zhì)是以不同的語言符號來表達(dá)同一思想,目標(biāo)是重現(xiàn)原文意義。因此,翻譯首先是譯者對原文思想內(nèi)容和表現(xiàn)方式的闡釋,而譯者把原文意義轉(zhuǎn)變?yōu)樽g文又是另外一個闡釋過程。而闡釋學(xué)就是解釋意義、探索意義的學(xué)科。因此現(xiàn)代闡釋學(xué)理論對翻譯研究很有借鑒意義。
譯者是翻譯活動的主體,是源語與譯語、源語文化與譯語文化的中介。而主體性則是主體的本質(zhì)特性。“具體地說,主體性是指主體在對象性活動中本質(zhì)力量的外化能動地改造客體,影響客體,控制客體,使客體為主體服務(wù)的特性”。譯者主體性最重要的特征是譯者的主觀能動性,譯者作為翻譯主體,一方面在進(jìn)行翻譯之前,要充分調(diào)動自己的主觀能動性認(rèn)真理解原文,另一方面進(jìn)入翻譯階段后,又要把自己作為原文的闡釋者,充分發(fā)揮自己的文學(xué)審美力和分析能力,分析原文作品的思想內(nèi)涵,使譯文再現(xiàn)原作的風(fēng)格與內(nèi)涵。可以說譯者的主體性就是指譯者在接受原作并在充分尊重原作的前提下,為了完成譯入語的文化要求和讀者要求而表現(xiàn)出的主觀能動性,其基本特征是譯者的自主性、能動性和創(chuàng)造性。譯者的主觀能動性應(yīng)貫穿于翻譯活動的始終,其主體性不僅應(yīng)體現(xiàn)在譯者對原作的選擇、理解和闡釋上,還應(yīng)體現(xiàn)在翻譯策略上。
二、譯者主體性的具體表現(xiàn)
譯者的主體性可以體現(xiàn)在很多方面,首先體現(xiàn)在譯者對文本理解和闡釋的過程。翻譯過程不僅僅是單純的語言之間的轉(zhuǎn)換,而是譯者在理解原文的基礎(chǔ)上再用譯入語加以闡釋的過程。譯者首先要作為讀者理解原作者的情感,這樣才能更好地向讀者傳達(dá)原文的信息。理解的過程也就是譯者與原作者達(dá)到視閾融合的過程。但是由于所處的時代、歷史、文化的不同,譯者的視閾不可能與原作者的視閾完全融合,不可能完全體會原作者的意圖。在伽達(dá)默爾看來,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理解文本的方式,所以文本的意義應(yīng)該由闡釋者所處的歷史環(huán)境決定。譯者不同的文化歷史背景使他們在理解文本的過程中產(chǎn)生差異,從而在很多地方的理解都會出現(xiàn)不同,甚至在整體風(fēng)格上也會各異,但是譯者有權(quán)根據(jù)自己的理解作出不同的闡釋。
其次,我們還可以從譯者對翻譯方法的選擇來看。譯者的審美情趣、語言風(fēng)格、翻譯目的、文化背景及自身的文化價值觀都會影響其對翻譯策略的選擇。一般來說,文學(xué)作品的翻譯特別是詩詞的翻譯更能體現(xiàn)譯者的主體性。因?yàn)樵娫~最能反映原作者獨(dú)特的個性、語言特點(diǎn)以及當(dāng)時的時代背景,而譯者的“視閾”想要與原詩達(dá)到融合,必然要充分發(fā)揮其主體性,使自己融入到原詩中去。本文擬從譯者的不同翻譯策略方面討論《紅樓夢》中林黛玉詩歌《題帕三絕句》兩個英譯本譯者主體性的體現(xiàn)。
三、林黛玉詩歌《題帕三絕句》兩英譯本對比
《紅樓夢》被稱為中華文化的百科全書。到目前為止,它已有九種英譯本,其中兩個最著名的譯本分別為楊憲益和其夫人戴乃迭所譯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 和大衛(wèi)?霍克斯及其學(xué)生約翰?閔福德所譯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這本不朽著作的一個顯著特點(diǎn)就是它包含兩百多首詩歌。詩歌作為最精練的文學(xué)體裁,是《紅樓夢》中所有人物描寫的集中體現(xiàn)。在《紅樓夢》的所有詩歌中,女主人公林黛玉的詩歌是其精華,她的詩歌充分體現(xiàn)了其性格特征與人文情懷。她的詩歌用詞極其精練,藝術(shù)手法最為典型,因此研究林黛玉詩歌的英譯在整個《紅樓夢》詩歌翻譯研究領(lǐng)域具有典型意義。
《題帕三絕句》寫于寶玉被笞,黛玉前去慰問,回去后接到寶玉托晴雯送來用過的手帕,心中有感而書寫三絕句于帕上,寄寓林黛玉對寶玉的深深愛戀和思念,以及自己無可排遣的哀傷情緒,也是林黛玉發(fā)自內(nèi)心深處的愛情宣言。這三首詩通篇寫淚,借以體現(xiàn)絳珠仙子還淚說的本原,第一首是明寫,直抒胸臆,明自如話。第二和第三首則暗寫,諸句不寫淚而淚在。以下我們從兩譯者不同的翻譯策略討論他們各自主體性的發(fā)揮。
《題帕三絕句》(一):
眼空蓄淚淚空垂,暗灑閑拋卻問誰?
尺幅鮫綃勞解贈,叫人焉得不傷悲!
楊譯:Vain are all these idle tears,
Tears shed secretly――for whom?
Your kind gift of a foot of gauze
Only deepens my gloom.
霍譯:Seeing my idle tears,you ask me why
These foolish drops fall from my teeming eye;
Then know,your gift,being by the merfolk made,
In merman’s currency must be paid.
這首詩原是林黛玉自己內(nèi)心感受的抒發(fā),楊譯文基本如實(shí)傳達(dá)了原詩的意思,采取直譯的翻譯策略,保持了原詩的含蓄之情,符合中國古代男女表達(dá)情感的內(nèi)斂含蓄。而霍克斯充分發(fā)揮了其作為譯者的主動性,譯文中出現(xiàn)了一個發(fā)問者“你”(you ask me why),把原詩中的淚譯為“foolish drops”,使得原詩的情意變得直接明快,這在一方面也顯示了西方人在表達(dá)情感的直接和熱情,但在另一方面卻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原詩的含蓄。這首詩楊譯較含蓄得當(dāng),略勝霍譯。
《題帕三絕句》(二):
拋珠滾玉只偷潸,鎮(zhèn)日無心鎮(zhèn)日閑。
枕上袖邊難拂拭,任他點(diǎn)點(diǎn)與斑斑。
楊譯:By stealth I shed pearly years,
Idle tears the livelong day;
Hard to wipe them from sleeve and pillow,
Then suffer the stains to stay.
霍譯:Jewelled drops by day in secret sorrow shed
Or,in the night-time,in my wakeful bed,
Lest sleeve or pillow they should spot or stain,
Shall on these gifts shower down their salty rain.
此詩為暗寫流淚,整首詩沒有出現(xiàn)“淚”字,但是楊譯出現(xiàn)了“pearly years”,“idle tears”,雖明白無誤表達(dá)了原意,但是缺乏整首詩含蓄的意境美。而霍譯用了“jewelled drops”,“salty rain”,形象而含蓄,充分體現(xiàn)了原詩含蓄優(yōu)雅的特點(diǎn),實(shí)屬佳譯。尤其是“secret sorrow shed”三個詞組成了頭韻,把林黛玉悲傷的形象描繪得入木三分。這說明霍克斯充分利用了譯入語優(yōu)勢,積極而富有成效地發(fā)揮了其譯者主體性,使譯文達(dá)到與原文一樣的美學(xué)效果,而楊譯略遜一籌。
《題帕三絕句》(三):
彩線難收面上珠,湘江舊跡已模糊。
窗前亦有千竿竹,不識香痕漬也無?
楊譯:No silk thread can string these pearls;
Dim now the tear-stains of those bygone years;
A thousand bamboos grow before my window
Is each dappled and stained with tears?①
①Referring to a kind of bamboo with dark spots.According to a Chinese legend,after King Shun died,his two wives mourned for him and their tears made dark spots on the bamboo.
霍譯:Yet silk preserves but ill the Naiad’s tears:
Each salty trace of them fast diappears.
Only the speckled bamboo stems that grow
Outside the window still her tear-marks show.
此詩中“湘江舊跡”是中國古代的傳說,古王舜去世后,其兩妃子娥皇和女英為其哀悼,淚水沾竹,留下黑色印跡,遂稱為斑竹。從翻譯策略上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楊譯千方百計使譯文保持原汁原味,旨在向西方讀者傳播中國文化,因此對原詩中“湘江舊跡”的典故采取異化的翻譯策略,并且加注,使得譯文讀者很好地理解此詩中典故的內(nèi)涵,從而使中國文化得到了有力的傳播。而霍譯充分發(fā)揮了譯者主體性,把原文譯為“Naiad’s tears”,Naiad(那伊阿得斯)是希臘神話中的水泉女神,霍克斯的翻譯目的是為了便于西方讀者理解,采取歸化的翻譯策略,直接用西方神話取代了東方神話,雖然西方讀者閱讀起來倍感親切流暢,但是他們永遠(yuǎn)不會知道“二妃哭舜”的中國神話了,這不利于中西方文化間的交流與傳播。本人傾向于楊譯,力圖傳播中國文化。
結(jié)語
闡釋學(xué)為翻譯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視角,它凸顯了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主體性地位,強(qiáng)調(diào)譯者是翻譯活動的中心。在原著面前,譯者必須發(fā)揮自身的藝術(shù)才能和主觀能動性,進(jìn)行堪與原著相媲美的再創(chuàng)作。同時還必須盡量忠實(shí)于原著,自覺用原著來約束自己。盡管楊憲益和霍克斯在翻譯林黛玉詩歌《題帕三絕句》時都著力于再現(xiàn)原著的意境與文化內(nèi)涵,但由于兩位譯者持有不同的翻譯目的、審美情趣和文化價值觀,因此對原文進(jìn)行了不同的闡釋,在翻譯過程中也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翻譯策略,從而使兩譯本彰顯了譯者不同的主體性。但是他們都較全面地傳達(dá)了原詩的基本思想,做到了基本尊重原文與適當(dāng)發(fā)揮主體的辯證統(tǒng)一。闡釋學(xué)以其獨(dú)特的視角體現(xiàn)了譯者在翻譯活動中的主體性,推動了翻譯理論的發(fā)展。隨著譯者主體性日益得到重視和發(fā)揮,我國的譯論必將發(fā)展得更快更好。
參考文獻(xiàn):
[1]Hawkes,D.The Story of the Stone[M].London:Penguin Books,1973.
[2]Yang Xianyi and Gladys Yang.A Dream of Red Mansions[M].Beij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99.
[3]蔡義江.紅樓夢詩詞曲賦評注[M].北京:中華書局,2001.
[4]曹雪芹,高鶚.紅樓夢[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7.
[5]葛校琴.后現(xiàn)代語境下的譯者主體性研究[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
[6]伽達(dá)默爾.真理與方法[M].洪漢鼎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
[7]屠國元,朱獻(xiàn)瓏.譯者主體性:闡釋學(xué)的闡釋[J].中國翻譯,2003,(6).
[8]謝天振.譯介學(xué)[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9.
[9]許鈞.“創(chuàng)造性叛逆”和翻譯主體性的確立[J].中國翻譯,2003,(1).
摘要:徐志摩是一位浪漫主義詩人,但他卻對英國批判現(xiàn)實(shí)主義詩人托馬斯?哈代情有獨(dú)鐘。而他的詩作與哈代的詩作也有很多共通之處。如其《問誰》與哈代的《黑暗中的鶇鳥》具有共通的創(chuàng)作背景、悲觀氣息和詩歌意象。
關(guān)鍵詞:徐志摩 哈代 詩歌 悲觀 意象 共通性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
徐志摩(1896-1931),浙江寧海人,新月派的代表詩人。1921年赴英國留學(xué),在劍橋兩年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并在歐美浪漫主義和唯美派詩人的影響下,開始創(chuàng)作新詩。托馬斯?哈代(1840-1928),英國詩人、小說家。哈代是橫跨兩個世紀(jì)的批判現(xiàn)實(shí)主義作家,其早期和中期的創(chuàng)作以小說為主,繼承和發(fā)揚(yáng)了維多利亞時代的文學(xué)傳統(tǒng);晚年以其出色的詩歌開拓了英國20世紀(jì)的文學(xué)。在五四時期的中國文壇上,徐志摩擔(dān)當(dāng)了融合和傳播中西文化的重要角色,譯介了大量的外文作品。有趣的是,在他短短的一生中,不僅翻譯了哈代的二十多首詩歌,而且曾四次撰文或賦詩對這位老人進(jìn)行追憶和憑吊。徐志摩對這位英國詩人極為崇敬仰慕,稱他為“老英雄”。美國著名中國文學(xué)專家西利爾?伯奇曾說:“我認(rèn)為,如果無視徐志摩對哈代的崇敬仰慕和偶然模仿,就不能解釋他詩歌生涯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即它的憂郁。”翻開徐志摩四部詩集中的任何一部,人們會發(fā)現(xiàn),在他那熱烈奔放、才思煥發(fā)、戀情熾熱的詩篇中,還夾有一類充滿驚人而深刻的哀怨的詩。
《問誰》來自徐志摩自己選編的《志摩的詩》,這部詩集主要表現(xiàn)了對人生自由的向往和對戀愛自由的渴望。但《問誰》這首詩卻流露出作者的人生理想在現(xiàn)實(shí)中遭到碰壁后的悲觀主義氣息。
《黑暗中的鶇鳥》表達(dá)了哈代面對風(fēng)雨飄搖的社會而產(chǎn)生的懷疑,對人類前途懷有的困惑。英國詩人阿爾弗雷德?諾伊斯曾對此詩作過這樣的評價:“這是我們這種抒情的語言所能寫出的最出色的哀怨動人的抒情詩……”《問誰》與《黑暗中的鶇鳥》在創(chuàng)作背景與個人心態(tài)、詩歌意象等方面擁有諸多的共通性。
一 共通的創(chuàng)作背景和悲觀氣息
關(guān)于徐志摩的思想,曾說過:
“他的人生觀真是一種‘單純信仰’,這里面只有三個大字:一個是愛,一個是自由,一個是美。他夢想著三個理想的條件能夠會合在一個人生里,這是他的‘單純信仰’。他的一生歷史,只是追求這個‘單純信仰’的實(shí)現(xiàn)的歷史。”
然而,由于生于中國一個特定的歷史年代:19世紀(jì)末20世紀(jì)初的中國。詩人的信仰在階級社會里根本不可能實(shí)現(xiàn),當(dāng)然會碰壁、會失敗。詩人逐漸變得消極,產(chǎn)生懷疑和悲觀的情緒。另一方面,他的愛情和婚姻的破滅也為他帶來更多的苦悶消沉:1922年3月,徐志摩向發(fā)妻張幼儀提出離婚,并試圖與林徽因繼續(xù)新的愛情,但他們的愛情卻并沒有結(jié)果;之后與陸曉曼的婚姻更是一個錯誤。詩人的愛情與婚姻的經(jīng)歷表明,他的理想主義的理想人生在現(xiàn)實(shí)社會不能得以實(shí)現(xiàn),從而也為他的詩歌蒙上了悲涼的氣氛。《問誰》就誕生于這樣一個時期,詩的開頭寫道:
啊,這光陰的撥弄/問誰去聲訴/在這冷沉沉的深夜,凄風(fēng)/吹拂她的新墓。
頹廢的基調(diào)已經(jīng)定了下來,詩人心中的苦悶不吐不快。死亡是幻滅的體現(xiàn),但他還懷有一線希望:
因此我緊攬著我的生命的繩網(wǎng)/像一個守夜的漁翁/兢兢業(yè)業(yè),注視著那無盡的時光/期冀有彩鱗掀涌。
可是,現(xiàn)實(shí)是殘酷的:
但如今,如今只余這破爛的漁網(wǎng)/嘲諷著我的希望/我喘息地悵惘著不復(fù)返的時光/淚依依的憔悴。
遠(yuǎn)處的村火、星星似乎透射出一點(diǎn)點(diǎn)希望的光芒,但傷心的人兒不敢直面人生,希望能永遠(yuǎn)活在這幻想之中:
但愿天光更不從東方/按時地泛濫/我便永遠(yuǎn)依偎在這墓旁/在沉寂里消幻。
這時的詩人還未被悲觀的情緒吞沒,黑暗中隱隱覺得還有一線光芒和希望:
但青曦已在那天邊吐露/蘇醒的林鳥/已在遠(yuǎn)遠(yuǎn)間相應(yīng)的喧呼/又一度清曉/不久,這嚴(yán)冬過去,冬風(fēng)/又來催促青條/便妝綴著冷落的墳?zāi)?也不無花草飄飄。
春天的氣息在感染著詩人,生命的力量也在溫暖漸漸冰凍的心靈。希望似乎在前方招手,盡管詩人仍存有一絲懷疑:
但為你,我的愛,如今永遠(yuǎn)封禁/在無情的地下……/我更不盼天光,更無有春信/我的是無邊的黑夜。
詩的字里行間回蕩著詩人感傷和憂患的回聲,表現(xiàn)了詩人失望苦悶的悲觀情緒。
哈代的《黑暗中的鶇鳥》創(chuàng)作于1899年12月31日,恰在世紀(jì)之交。我們可以這樣推測:19世紀(jì)的最后一個黃昏,在那樣一個特別的日子里,年過半百的詩人,回顧往昔――自1800年起,英國依靠圈地運(yùn)動、海外掠奪和殖民統(tǒng)治積累原始資本,生產(chǎn)力得到迅猛發(fā)展,成為了“世界工廠”。現(xiàn)代機(jī)器的隆隆聲打破了農(nóng)村的寧靜,甜美、安詳、平靜的生活一去不返,取而代之的是浮躁喧嘩和混亂。面對現(xiàn)實(shí)的十字路口,哈代的心情緊縮得如冬日風(fēng)中瑟瑟發(fā)抖的鶇鳥,孤獨(dú)而凄涼:
我倚在以樹叢作籬的門邊/寒霜像幽靈般發(fā)灰/冬的沉渣使那白日之眼/在蒼白中更添憔悴。
“寒霜”、“幽靈”、“冬的沉渣”、“蒼白”,都在渲染一種蒼涼蕭瑟的氣氛,正如世紀(jì)交替時人們心中充滿懷疑的悲涼心情。
哈代破滅的不僅是理想的鄉(xiāng)村生活,宗教信仰的破滅也許給了他最大的打擊。19世紀(jì)后期,是西方科學(xué)與宗教激烈沖突的時代。達(dá)爾文提出了進(jìn)化論的科學(xué)觀點(diǎn),動搖了哈代與生俱來的上帝造人的宗教信仰。同時,1896年問世的《無名的裘德》受到了外界諸多的質(zhì)疑和攻擊,內(nèi)心極度痛苦的哈代遂放棄小說寫作,傾注全力于詩歌,并且常常表達(dá)出對陰郁環(huán)境的哀愁和悵惘,正如詩中所寫道:
陸地輪廓分明,望去恰似/斜臥著世紀(jì)的尸體/陰沉的天穹是他的墓室/風(fēng)在為他哀悼哭泣。/自古以來萌芽生長的沖動/已經(jīng)收縮的又干又硬/大地上每個靈魂與我一同/似乎都已喪失熱情。
這里的“尸體”、“陰沉”、“墓室”更加直接地反映出哈代此時的心態(tài)已接近絕望。然而,哈代并不是一個悲觀主義者,他在其《道歉》中說道:
“如今對本作者的作品所提出的‘悲觀主義’,事實(shí)上只是對現(xiàn)實(shí)探索上的倔強(qiáng)的疑問……這是修繕心靈,也是修繕人體的第一步。”
由此可見,哈代在悲觀中的剛強(qiáng)。哈代歷來反對稱他為悲觀主義者,自稱是社會向善論者。他曾經(jīng)多次申明:“作為向善論者,我對世界抱有信心。”詩中第三節(jié)筆鋒一轉(zhuǎn),描寫了一只歡唱的鶇鳥,令人精神為之一振:
突然間,頭頂有個聲音/在細(xì)枝蕭瑟間升起/一曲黃昏之歌滿腔熱情/唱出了無限欣喜。/ 這是一只鶇鳥,瘦弱,老衰/羽毛被陣風(fēng)吹亂/卻決心把它的心靈敞開/傾瀉向濃濃的黑暗。
鶇鳥的歡唱沖淡了前兩節(jié)詩中的悲觀情緒,預(yù)示著新的世紀(jì)可能會帶來一點(diǎn)生機(jī),也讓我們感受到了鶇鳥在艱難的生存環(huán)境中所表現(xiàn)出的頑強(qiáng)的生存意識、旺盛的生命力和樂觀精神。
歷史的大背景與個人的不幸遭遇交織在一起,造就了兩首悲觀中透著希望的詩,正如徐志摩對哈代的體會:
“湯麥?zhǔn)?哈代吹了一輩子厭世的悲調(diào); 但是一只冬雀的狂喜的狂歌, 在一個大冷天的最凄涼的境地里,竟使這位厭世的詩翁也有一次懷疑他自己的厭世觀,也有一次疑問這絕望的前途也許還閃耀著一點(diǎn)救度的光明。”
在徐志摩眼里, 哈代是反抗悲觀的深沉的英雄,他自己也從中獲得了“靈魂探險的勇氣”。
二 共通的詩歌意象運(yùn)用
詩歌作為一門審美情感具像形態(tài)的藝術(shù),是“將審美情感物化為詩的意象,然后依著詩人情感活動的脈絡(luò)、軌跡富有個性地組成意象,以意象結(jié)構(gòu)顯現(xiàn)感情結(jié)構(gòu),傳達(dá)情感”。所以,意象是詩歌內(nèi)在構(gòu)造的基本元素。在這個意義上,雖然不能把意象作為檢驗(yàn)一首詩的試金石,但可以肯定的是,一首好詩在意象運(yùn)用上一定是成功的。因此許多詩人往往致力于以“生花夢筆垂麗天之象”,極盡造奇之能事。在《問誰》與《黑暗中的鶇鳥》中,一些原本日常所見的平常意象訴諸讀者的感官,調(diào)動了讀者的想象,如《問誰》中的深夜、凄風(fēng)、新墓、黑夜、黑影、新墳、曠野、嚴(yán)冬;《黑暗中的鶇鳥》中的寒霜、冬、藤蔓、尸體、墓室、風(fēng)。
兩首詩中所營造的凄清寒冷的境界竟是如此的相似,詩人將簡潔的意象組成一幅蕭瑟凄迷的圖景,以感情的邏輯組合意象,將題旨指向的平面感用立體交叉的意象流動地呈現(xiàn)出來。意象是具體化了的感覺,詩的意象是情意化了的形象。
死亡,作為人物質(zhì)生命的終結(jié),長久以來在中西方的傳統(tǒng)文化中帶給人深重的焦慮和困擾,成為與美對立的丑的存在,連飄逸灑脫的徐志摩也不得不承認(rèn)它的不吉利。但在徐志摩的詩文創(chuàng)作中,人們看到的卻多是鮮花青草相伴的靜謐的墓園,死亡成了解脫和自由的天國。值得注意的是:徐志摩對墓園和死亡的美麗想象是建立在他對死亡的悲劇性深刻體認(rèn)之上的。這其中的二律背反,正折射了徐志摩死亡意識的矛盾性和復(fù)雜性。徐志摩在致友人凌叔華的信中說:
“我的想象總脫不了兩樣貨色,一是夢,一是墳?zāi)梗坪醪淮蠼】担皇羌页T诤诘乩飿?gòu)造意境,其實(shí)是太晦色了……”
然而,在《問誰》中,盡管詩中重復(fù)出現(xiàn)了這樣的意象:新墓、黑夜、黑影、新墳、曠野、嚴(yán)冬,但全篇卻傳達(dá)出道家死亡哲學(xué)的痕跡:中國傳統(tǒng)的道家文化消解了死亡與生命的絕對對立,認(rèn)為死亡是與此在人生相通的彼在世界,徐志摩對墓園的美麗想象,在努力消解死亡的悲劇性并對死后的美好產(chǎn)生的期待與預(yù)設(shè),就得益于道家文化的熏染。
哈代在意象運(yùn)用上確有獨(dú)到之處,無論在小說還是在詩歌創(chuàng)作中,哈代都是一位擅長描寫自然的作家,自然意象在揭示主題、塑造形象方面,起著畫龍點(diǎn)睛的神奇效果。在《黑暗中的鶇鳥》這首詩中,作者為了傳達(dá)這樣一種信息――希望,創(chuàng)造了這樣幾個意象:寒霜、冬日、藤蔓、陸地、天穹、風(fēng)、鶇鳥。詩人通過這幾個原本日常所見的平常意象訴諸于讀者的感官,調(diào)動讀者的想象。詩歌一開始,向讀者推出了一組凄清慘淡的鏡頭:寒霜幽靈般地降臨大地;冬天的乏味好比是咖啡壺底的渣滓;白日則像一個忙碌的婦人眼神倦怠;藤蔓糾纏在一起像斷弦一團(tuán),徒增傷感;萬籟俱靜,不見人影。
就在滿目蕭瑟、一片死氣沉沉之時,突然一曲歡歌打破了沉寂。此時詩人充分利用視覺效果,歌聲不是由細(xì)枝間傳來而是“升起”,仿佛是一束明光穿透了漸濃的黑暗,它使人們心中久已熄滅的希望之火得以重新點(diǎn)燃。“只聞鳥聲,不見鳥影”,讀者不禁會想象:寒風(fēng)中放歌的鳥該是正當(dāng)盛年吧?但接下來,詩人卻描繪了這只鶇鳥的瘦弱和衰老。這必是大大出人意料的一筆,惟有仔細(xì)尋味才能領(lǐng)悟到詩人的良苦用心。這只顯然久經(jīng)風(fēng)雨的鶇鳥在逆境中毫不沮喪,敢于迎接黑暗(象征死亡)的挑戰(zhàn);敞開心扉,是因?yàn)樗闹袘延袑π腋5南MH缜八觯莻€宿命論者,所以他選擇了一系列灰暗、殘損的意象,這一點(diǎn)已經(jīng)為我們所理解。但在這里,鶇鳥這一意象為何又體現(xiàn)了與前面詩節(jié)迥異的情感?這是因?yàn)椋鳛槭灞救A信徒的哈代同時又是達(dá)爾文進(jìn)化論的弟子;他在對人類未來深感悲觀的同時,又相信人類社會會進(jìn)步、會發(fā)展。其矛盾的思想體現(xiàn)在詩歌中,便出現(xiàn)了這種前后情感意象分庭抗禮的局面。也正因此,在詩歌結(jié)尾,詩人才會發(fā)出“它歡樂的晚安曲調(diào),含有某種幸福希望――為它所知,而不為我所曉”的感嘆。
徐志摩詩作中的一些特定形象和事件或創(chuàng)作技巧及風(fēng)格也許是無意中模仿了哈代,但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都使徐志摩受益匪淺。因有感于哈代,所以徐志摩對哈代詩歌的吸收和借鑒都是從詩的本身內(nèi)涵出發(fā),而非單純地模仿。也正因此,他能創(chuàng)作出自己最優(yōu)秀的詩篇。
參考文獻(xiàn):
[1] :《志摩紀(jì)念號EJ》,《新月》,1932年第4期。
[2] 哈維?韋伯斯特:《在黑暗的平原上:湯姆士?哈代的藝術(shù)與思想》,康涅狄克州出版社,1964年版。
[3] 徐志摩:《迎上前去》,《徐志摩全集》(第三卷),廣西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
[4] 飛白、關(guān)笛譯:《夢幻時刻――哈代抒情詩選》,中國文聯(lián)出版公司,1992年版。
[5] 張中載:《托馬斯?哈代――思想和創(chuàng)作》,外語教學(xué)與研究出版社,1997年版。
我曾經(jīng)在給《人民文學(xué)》評年度獎的時候給劉年的組詩《虛構(gòu)》寫過頒獎詞:“組詩《虛構(gòu)》是真實(shí)之詩,也是寓言之詩。他的贊美與批判不僅關(guān)涉?zhèn)€體性的現(xiàn)實(shí)而且還關(guān)乎深層的命運(yùn)感以及歷史想象能力。他游走‘邊地’的抒寫撥現(xiàn)了‘地方性知識’在城市化時代的重要性。他詩歌的體溫灼熱滾燙,同時又冷靜自持,可貴的是還持有疏離和提升的能力。這是一個樸素、厚道、可靠的寫作者。他自我縮減的謙卑與敬畏的同時正是周邊秘世界不斷打開的過程。個體烏托邦意義上的精神吁求適度而又讓人心懷渴念。”那次頒獎是在魯迅文學(xué)院。頒獎結(jié)束時已是黃昏。我乘公交回家,而劉年則去趕著另一個酒局。期間,我們一句話也沒說,像極了兩個不相干的人。而最早接觸劉年,還是在滇南的第28屆青春詩會上。那時的劉年只是一個“編外”的參會者。我記得他穿著類似于職業(yè)攝影師的褪了色的藍(lán)色馬甲,背著一個仿軍用的綠色雙肩背包,或扛或端著一個大塊頭的攝像機(jī)。劉年話非常少,乍一看還以為是隨行的挑夫或馬夫。在青春詩會結(jié)束后,我看到了那張他坐在滇南山中隧道鐵軌上的照片。我想起了那時的驚雷滾滾和瓢潑大雨,想到一行人在泥濘和風(fēng)雨中艱難徒步。那么他們行走和寫詩的最終目的是什么呢?在我看來這次行走實(shí)際上最接近于詩歌的本質(zhì)――過程如此艱難,且結(jié)局也充滿了諸多的不可預(yù)見性。而詩歌帶給我們的安慰就如隧道盡頭忽隱忽現(xiàn)的亮光。我們有時候是飛蛾,愿意撲火。
劉年,本名劉代福。這一個“福”字的氣息讓我想到的是鄉(xiāng)下漆黑門框上手寫的粗黑大字,聞到的是嗆人的劣質(zhì)煙草背后的樸素而溫暖的愿望。但是,為了這一“福”字你必須付出代價。我最初以為劉年是云南人,后來才知道他是湘西永順人。是的,劉年的詩歌中有烈酒氣和冷森森直挑命門的劍氣。但這種烈氣和劍氣更多的是傷害自己。這種酒氣和烈氣在胸中攪拌、蒸騰后就激蕩成了一條大江。它們澎湃的時候驚天動地,它們安靜的時候讓你黯然神傷。我一次次在劉年的詩歌中看到他在江邊蹲坐或躺臥,或者小獸一般的低低吼叫。后來劉年來北京,我們的見面也大體是在會場和飯桌上。感覺劉年喝酒不如以前那么生猛了,也不怎么直接跟我叫板了。在海南的夜色中,劉年穿著衣服短褲頭直接撲進(jìn)了黑沉沉的大海。而一次在我老家唐山曹妃甸濕地,他從船上也是直接跳進(jìn)了水里。撲騰的水浪和渾濁的漩渦在那個北方的下午一直在攪動……
雷平陽曾說劉年是中國最具有騎士精神的詩人,于是不知道從何時開始劉年在我這里就突然改頭換面成了劉騎士。而我每次見面也都高聲喊他――“劉騎士”。盡管是一句看起來有些搞笑的說辭,卻在內(nèi)里上抵達(dá)了一個詩人的精神內(nèi)核。是騎士,當(dāng)然要有騎士精神。這自然缺不了一匹快馬和一柄長劍,腰間也少不了一個酒葫蘆,“有必要,虛構(gòu)一個我,寫字的這個,皺紋太多 /在臉上,虛構(gòu)一些笑容,在腰間,虛構(gòu)一柄長劍 /因?yàn)楝F(xiàn)實(shí)太硬,劍,有必要虛構(gòu)它削鐵如泥”(《虛構(gòu)》)。馬用來閑蕩遠(yuǎn)游,劍也并不是簡單的武器而是成了騎士的一個象征之物。當(dāng)轉(zhuǎn)換為詩人,“劉騎士”的馬和劍和酒在詩歌中不斷出現(xiàn)疊加。與此同時,我也越來越看到一個漸漸疲累的劉年,人到中年而胸中塊壘并未曾全部融化的劉年。
有時候詩人就是給自己貼上“尋人啟事”的人。是的,這必然是一個虛構(gòu)出來的“劉騎士”――“有必要虛構(gòu)一些紙,記錄一些即將焚毀的事實(shí) /然后虛構(gòu)一些事實(shí),祭奠那些誠實(shí)的化為灰燼的紙”。實(shí)際上這一文字化的“騎士”是維持了個體主體性的“一個人”真實(shí)存在空間的支撐點(diǎn)。盡管這一支撐最終在強(qiáng)大的現(xiàn)實(shí)面前也必然是虛無和癱毀的。而在內(nèi)里上而言,尤其是精神性強(qiáng)大的詩人與“苦行僧”是相互打開彼此共通的。而為了維持一種固有的根性,詩人又必然承擔(dān)起挖掘人和汲水者甚至土撥鼠的角色,“時間和茂盛的言詞不足以埋葬一切 /一定能找到破碎的瓷器,證明歷史的骨頭 /一定有土撥鼠在挖掘老栗樹的根 /于是,我把這個靜如墳?zāi)沟膹U墟,命名為繁華”。最終淘洗上來的只是碎片和骨殖以及斷根,連同帶上來的還有黑夜一樣的虛無無著。那么詩人就不能不虛妄、反諷、悖論,在修辭學(xué)上也不期然地成了“言不由衷”“口是心非”的人,成了魯迅筆下面對著墳?zāi)购痛鼓豪先艘约半[蔽在荊棘叢中小路上的夜行人。
劉年前一段時間也突然成了文壇關(guān)注的熱點(diǎn)。
眾所周知是他最早在網(wǎng)絡(luò)上發(fā)現(xiàn)了湖北一個叫余秀華的詩人。在余秀華還不為人知的時候,在一次詩歌評選活動中,我是第一次集中閱讀了余秀華的詩,我當(dāng)時沒有想到她是一個腦癱者,而只是從詩人和詩歌的角度來衡量她的詩。在那一批參評的 70后和 80后的詩人當(dāng)中,余秀華的詩是突出的。而當(dāng)她成了中國文壇和文化界的一個事件,人們談?wù)摳嗟牟⒉皇撬脑姼瑁撬哪X癱、農(nóng)婦和底層的身份。目下人們對余秀華或者談?wù)摰眠^多,或者不屑一顧(尤其是在所謂的“專業(yè)詩人”圈內(nèi)),但是真正細(xì)讀余秀華詩歌的人倒是不多。撇開那些被媒體和標(biāo)題黨們?yōu)E用和夸大的《穿越大半個中國去睡你》,擱置詩歌之外的余秀華,實(shí)際上余秀華很多的詩歌是安靜的、祈愿式的。而她那些優(yōu)秀的詩作則往往是帶有著“贊美殘缺世界”態(tài)度的,盡管有反諷和勸慰彼此糾結(jié)的成分,比如她在 2014年冬天寫下的《贊美詩》――“這寧靜的冬天 /陽光好的日子,會覺得還可以活很久 / 甚至可以活出喜悅 //黃昏在拉長,我喜歡這黃昏的時辰 / 喜歡一群麻雀兒無端落在屋脊上 /又旋轉(zhuǎn)著飛開 //小小的翅膀扇動淡黃的光線 / 如同一個女人為了一個久遠(yuǎn)的事物 /的戰(zhàn)栗 //經(jīng)過了那么多灰心喪氣的日子 /麻雀還在飛,我還在搬弄舊書 /玫瑰還有蕾 //一朵云如一輛郵車/好消息從一個地方搬運(yùn)到另一個地方 /仿佛低下頭看了看我”。
余秀華來北京參加在人民大學(xué)舉辦的詩歌朗誦會的時候還專門給劉年提了一籃子雞蛋。后來看到劉年,我就開他玩笑,“土雞蛋吃了效果確實(shí)不一樣啊,越來越精神和高大上了。”余秀華不僅送雞蛋,而且還送詩給劉年,而這才是真正的詩人之間的相互理解和精神會心吧――“風(fēng)吹四月,吹平原麥浪,麥芒響亮。/一個男子在麥地里走,山在遠(yuǎn)方 //灰房子,紅房子,一個院子里曾晾曬他衣裳 /一個男子站在山腰上,風(fēng)吹紅他胸膛 //人間俱綠,形同哀傷 / 他的影子倒映在夕光上,海在遠(yuǎn)方 //他的呼吸輕,但天地有回聲 /一棵野草也跟著搖晃 //他說:萬物生 / 我也在其中”。
從詩歌編輯的角度來說,劉年是有眼光和判斷力的。那么具體到劉年自身的詩歌,我們該談?wù)撌裁茨兀?/p>
劉年的詩歌在空間上讓我們迎面與城市和鄉(xiāng)村同時相撞,他是典型的焦灼痛感式寫作的樣本。說句實(shí)在話,劉年通過對城市和鄉(xiāng)村以及自然空間的精神性再造讓我們發(fā)現(xiàn)了日常的熟悉的又莫名陌生的“現(xiàn)實(shí)”。任何人都不能回到過去也難以超越當(dāng)下,而恰恰是被二者之間的瓶頸處卡在那里艱難地喘息。劉年就是如此,企圖再次坐上粗糙破舊但是溫暖的牛車回到多年前緩慢的黃昏是不可能了。與此同時,在非虛構(gòu)寫作和抒寫現(xiàn)實(shí)的底層和草根詩人那里,恰恰相反,我卻看到那么多的文學(xué)文本并沒有提供給我們認(rèn)識自我和社會現(xiàn)實(shí)的能見度。盡管我在美國人海斯勒的《尋路中國》《江城》那里也獲得了一種認(rèn)識中國的另外一個途徑,但是作為一個“旁觀者”海斯勒還是缺乏更為真切的本土性的清醒和自審。2012年 7月 21日,北京。那場 60余年不遇的罕見暴雨并未散去!那突如其來的暴雨甚至超出了我們對日常生活與龐大現(xiàn)實(shí)的想象極限。而在秩序、規(guī)則和限囿面前,我們卻一次次無力地垂下右手。在我看來新世紀(jì)以來的中國知識分子面對強(qiáng)大而難解的社會現(xiàn)實(shí)所相對的卻是空前的難以置喙和無力。這可能會引起人們的不解。我們不是有那么多與社會現(xiàn)實(shí)聯(lián)系密切的文學(xué)嗎?是的,由這些文本我們會聯(lián)想到那些震撼和噩夢般的現(xiàn)實(shí),但是與現(xiàn)實(shí)相關(guān)的文學(xué)就一定是言之鑿鑿的事實(shí)呈現(xiàn)嗎?面對“糟糕”的現(xiàn)實(shí)我們很容易因?yàn)椴粷M而在不自覺中充當(dāng)了憤青的角色――“我還記得八月中旬,臨行前和朋友們坐在北京世貿(mào)天階,談?wù)撝袊F(xiàn)實(shí)的種種,一種空前的庸俗感,讓我們倍感窒息”,“我厭惡那無處不在的中國現(xiàn)實(shí),是因?yàn)樗鼈儥C(jī)械地重復(fù)、毫無個性……它們一方面無序和喧鬧,另一方面又連結(jié)成一個強(qiáng)大的秩序”(許知遠(yuǎn))。而我想說的是我們對“現(xiàn)實(shí)”除了“厭惡”和“不滿”之外是否還需要更多其他的聲音(尤其是“異質(zhì)”的聲音)?中國的晚近時期的鄉(xiāng)村史、命運(yùn)史和波詭云譎的時代一起沖撞著微不足道的個體命運(yùn)。一定程度上我們所缺少和應(yīng)該堅(jiān)持的正是一種“羞恥的詩學(xué)”,只有如此方能對抗虛榮、權(quán)力、浮躁和假相。面對愈益紛繁甚至陌生的中國現(xiàn)實(shí),眾多的閱讀者和研究者顯然并未從田野考察的角度和歷史譜系學(xué)的方法關(guān)注普通人令人唏噓感嘆命運(yùn)遭際背后更為復(fù)雜的根源、背景、動因、策略和文化意義。這大體印證了米沃什的“見證詩學(xué)”。
劉年的詩歌和生命體驗(yàn)直接對話,有痛感、真實(shí)、具體,是真正意義上的“命運(yùn)之詩”。當(dāng)然,這種日常現(xiàn)實(shí)寫作的熱情也伴隨著一定的局限。很多詩人沒有注意到日常現(xiàn)實(shí)轉(zhuǎn)換為詩歌現(xiàn)實(shí)的難度,與此同時詩歌過于明顯的題材化、倫理化、道德化和新聞化也使得詩歌的思想深度、想象力和提升能力受到挑戰(zhàn)。這一現(xiàn)實(shí)景觀不是建立于個體主體性和獨(dú)特感受力基礎(chǔ)之上的“靈魂的激蕩”,而是淪為了“記錄表皮疼痛的日記”。很多詩人寫作現(xiàn)實(shí)的時候缺乏必要的轉(zhuǎn)換、過濾、變形和提升的能力。大多當(dāng)下的各種詩人大抵忘記了日常現(xiàn)實(shí)和詩歌“現(xiàn)實(shí)感”之間的差別。劉年曾在說到詩人趣味的時候簡略地提到詩歌的寫作和發(fā)生,他做了一個假想性的例子倒是很有意思,“詩人在寫不出詩的時候,應(yīng)當(dāng)坐七個小時的汽車,再轉(zhuǎn)三個小時的手扶拖拉機(jī),去鄉(xiāng)下找一個煮得一手好魚的朋友。”這也許就是重新發(fā)現(xiàn)自我和生活的過程,也大體印證了寫作與生活、經(jīng)歷的關(guān)系。或者說對于當(dāng)下很多的詩人而言,他們每天都在看似抒寫“現(xiàn)實(shí)”,但實(shí)際上他們太缺乏語言、修辭和想象力的“現(xiàn)實(shí)感”了。米沃什對二十世紀(jì)的詩人就批評過他們?nèi)狈@種“真實(shí)感”,而這到了二十一世紀(jì)的今天那些話卻仍然有效。所以,文學(xué)沒有進(jìn)化論,有的只是老調(diào)重彈卻時時湊效。而劉年恰恰通過多年的行走、田野踐行和個人化的歷史想象力重新發(fā)現(xiàn)了自我和現(xiàn)實(shí)。劉年曾在隨筆中主張文人應(yīng)該站在弱者的一方,實(shí)際上寫作者自身在現(xiàn)實(shí)生活中本來就是弱者。也許,精神性的自我可以聊以慰藉滾滾塵埃中的苦痛。而劉年也曾一度在倫理化的怨憤和批判中來面對城市化的生活,但是經(jīng)過調(diào)整他的視角和態(tài)度已經(jīng)具有了很大的包容性。是的,詩歌沒有容留性就很容易成為自我沉溺的“純詩”或大張旗鼓的日常化的仿寫和吆喝過市的低廉道德的販賣者。我們必須承認(rèn)文學(xué)的力量不在于像流行的“非虛構(gòu)寫作”一樣只是提供了淚水、苦難、傷痛的倫理學(xué)的印記,而是更為重要地為每一個人重新審視自己以及看似熟悉的“現(xiàn)實(shí)”提供一次陌生的發(fā)現(xiàn)性機(jī)會。
劉年的詩歌是不乏戲劇性的。當(dāng)年的艾略特曾將詩人的聲音分為三種,而無論是自我的獨(dú)語,廣場上的高聲宣講還是戲劇性的聲音都構(gòu)成了詩人眾多聲部中的重要所在。而就劉年而言,這種戲劇性的詩歌和聲部呈現(xiàn)的不僅是“命運(yùn)之詩”而且也是關(guān)涉現(xiàn)實(shí)與生存甚至整體性時代的“寓言之詩”。因?yàn)槟闳匀豢梢栽谠姼柚凶匝宰哉Z,但是更多的詩人抬高了聲調(diào)以便向身邊的人、大街上的人、車站里的人說些什么――盡管這些話在大眾和旁觀者那里的作用遠(yuǎn)不如黑夜里一根針掉落水泥地上的倏忽之音。劉年甚至也成了面孔略黑而赤紅的“講故事”的人,那些故事迷離倘恍又冷徹刺骨。甚至劉年詩歌中的敘事性和戲劇化的元素一度壓制了抒情性的空間,密度和緊張感以及撕裂程度前所未有。實(shí)際上這種寫作并不是個案,但是一定要提請注意的詩歌的方式與小說和非虛構(gòu)之間的本質(zhì)區(qū)別,反之很容易成為“敘事”的替代品或衍生物。這種戲劇性既來自于劉年自身的詩歌調(diào)性和話語方式,也來自于日常生活自身的吊詭怪誕和難解,“有一次,父親說,他最大的夢想是去周圍的縣市去轉(zhuǎn)一轉(zhuǎn)。我說這個太容易了,等買了車之后,我們一家就去轉(zhuǎn)。下一次回來,我才知道自己失去了一次多么寶貴的機(jī)會。世界上最遠(yuǎn)的距離,在生與死之間。”(《遠(yuǎn)》)這既是個人的現(xiàn)實(shí),又是鄉(xiāng)村的現(xiàn)實(shí),也是更為中國化的當(dāng)下現(xiàn)實(shí)。而由此生發(fā)出來的“戲劇性”對于很多人來說卻是悲劇,那么沉浸在悲劇性體驗(yàn)的人們該如何表達(dá)內(nèi)心的苦痛以及更為重要的具有普世性的聲音?比如劉年有這樣的詩句“剝開一個橘子,酸澀是故鄉(xiāng)的本質(zhì)”(《火塘》),“舊居,是方言 / 墳?zāi)沟囊馑肌保ā杜f居》),“布滿血絲的淚眼,是一生都逃不出的故鄉(xiāng)”(《游臘姑梯田,兼懷遠(yuǎn)人》)。據(jù)此,劉年也成了一個“病人”以及“故地”的“陌生人”,“畫張自畫像,像重癥肝炎病人一樣 / 讓自己散發(fā)著黃金般的光芒”(《黃金時代》)。故鄉(xiāng)是黑暗的充滿了病痛甚至死亡不祥氣息的所在,“故鄉(xiāng),是堂屋正中央 / 那一具漆黑的父親的棺材”(《故鄉(xiāng)》)。這既是個體的命運(yùn)遭際和家族命運(yùn),也是整體性意義上的鄉(xiāng)村寓言和精神癥候史。如果說這一新世紀(jì)以來的鄉(xiāng)村敘事對于文學(xué)史和中國社會史以及后來人還有意義的話,那就是多年之后的讀者在那些發(fā)黃的書頁間以及電子搜索引擎上看到的一個關(guān)鍵詞――苦痛。
而對于劉年來說,這種自嘲就是自審。我曾在很多文章中批評過新世紀(jì)以來詩人和寫作者們過去強(qiáng)烈的倫理化判斷。而我最終發(fā)現(xiàn)自己竟然也是其中的一員。那么,我對自己的反思也是對當(dāng)下寫作現(xiàn)實(shí)體驗(yàn)的詩人追問的是――這是否意味著詩歌要去接受“悲觀主義、諷刺、苦澀、懷疑的訓(xùn)練”?
說到命運(yùn)之詩,似乎也多少是一個可有可無的話題,因?yàn)檫@關(guān)乎每一個寫作者的本源性命題,只不過在特殊的歷史和現(xiàn)實(shí)節(jié)點(diǎn)上這一命運(yùn)更多是帶上了集體性的沉暗面影。而從新世紀(jì)以來一種“寓言之詩”正在發(fā)生。
這一寓言化的寫作所對應(yīng)的正是吊詭怪誕的現(xiàn)實(shí)生活,而生活以及生活背后的情感、文化和道德機(jī)制的真實(shí)性已經(jīng)超出了我們理解力和想象力的極限。也就是說這些詩歌相應(yīng)地顯得不太真實(shí)起來,但是在詩學(xué)和社會學(xué)的雙重層面這一“寓言之詩”卻又恰恰是可靠和有效的。如果你讀讀劉年的詩歌和隨筆等文字,你會發(fā)現(xiàn)一些場景、細(xì)節(jié)以及圍繞其上的象征性和精神氛圍介于真實(shí)和須有之間,恍如昨夢卻又真實(shí)發(fā)生。
既然是騎士,就得要去“遠(yuǎn)方”。
劉年這家伙看起來木訥、樸實(shí),但是內(nèi)心里有一個浪漫的柔軟的湖,只不過他隨時將烈酒投擲進(jìn)去,隨時也可以燃燒起來。這是一個明知沒有遠(yuǎn)方也要去涉險的執(zhí)拗的湘西人。這是一個即使撞得頭破血流但仍然懷有愿景和碎夢的家伙(比如他在一首關(guān)于洱海和詩人朋友的詩中將自己稱為“段譽(yù)”)。
劉年的詩歌有很多慣用的祈愿和祈使句式,“我想……”在他的詩歌中頻繁出現(xiàn)。這就是所謂的“現(xiàn)實(shí)白日夢”吧!劉年的這一祈愿總會讓我想到當(dāng)年海子的那句“我想有一所房子”中最關(guān)鍵的那個詞“想”。而這正是現(xiàn)實(shí)與主觀愿景和靈魂世界之間巨大的不對等性,其結(jié)果必然是沉暗莫名荊棘叢生的“精神無地”之所。如果你偏要再給這個時代的詩人帶上花環(huán),它也必然是荊棘編織而成。在此,《青海湖邊的木屋》《虛構(gòu)》《遙遠(yuǎn)的竹林》等就只能是個人虛幻的烏托邦了。而這可能就是詩人的終極責(zé)任或歸宿吧!
這是在實(shí)有和幻想的背包中放置了命運(yùn)信札的人。有一次同行外出,劉年竟然背著一個超乎想象的巨大背包,甚至這只包比劉年的個子還高。他似乎真的要決意遠(yuǎn)行了,可是不久他又出現(xiàn)在北京東三環(huán)的某個人聲鼎沸的酒桌上。
劉年參加青春詩會出版的詩集就命名為《遠(yuǎn)》。正如他自己所說――遠(yuǎn)方的遠(yuǎn),遠(yuǎn)去的遠(yuǎn),遠(yuǎn)不可及的遠(yuǎn)。這個拆遷法則下的時代空間正在被空前同一化,屏幕化的閱讀方式取代了行走的能力,真正的遠(yuǎn)方似乎已經(jīng)不再存在――所以“遠(yuǎn)方的遠(yuǎn)”不可能。那么“遠(yuǎn)去的遠(yuǎn)”作為過去時態(tài)和歷史就只能是作為一種記憶和追懷了。而“遠(yuǎn)不可及的遠(yuǎn)”所對應(yīng)的正是當(dāng)下無詩意的生活和存在狀態(tài),這產(chǎn)生的就必然是無望、虛妄和撕裂以及尷尬的體驗(yàn)和想象。而這三個虛無維度的“遠(yuǎn)”進(jìn)入到劉年的精神世界和詩歌文本當(dāng)中的時候,你面對的必然是粗糲、柔軟、狂醉、木然、不甘、絕望的混雜相聚。既然“遠(yuǎn)”已經(jīng)不現(xiàn)實(shí),那么劉年就只能近乎決絕式的將自己置放在人群、鬧市、客棧和異地、逆旅之中。他時時回顧尋找自己的馬匹和利刃,他也不得不一次次用烈酒去暫時麻醉自己,在霧霾的城市里面對已然逝去的鄉(xiāng)村的黃昏,面對彷徨于無地的精神鄉(xiāng)愁和一個浪子的回頭無岸。
值得注意的是劉年也有一些“輕體量”的詩(比如《青龍峽的夜》《恒河》《辛卯中秋》)、三四行左右的斷章體以及相當(dāng)數(shù)量的十行之內(nèi)的雙行體詩(如《游大昭寺》《老花鋪》《梅里雪山》《在可汗宮酒店的陽臺上》《深秋的睡蓮》《黃金時代》《隨想錄》《岡拉梅朵客棧》《草山的星空》《臨水塘小鎮(zhèn)》《水滴》《薩榮的月亮》《藏香》《從碧色寨到芷村》《湘西土匪》《野鹿河》《游臘姑梯田,兼懷遠(yuǎn)人》《隱居》《胡家村記事》《語滴》《油菜芽》《子夜書》等等)。我之所以羅列這些詩更多是想提醒劉年自己多想想,而劉年的意見是還將繼續(xù)寫所謂的雙行體。那就寫著瞧吧!劉年的這些詩大多形制短小,抒情自我化較為明顯,詩思也是碎片在寒夜的一閃而逝。但是,我認(rèn)為“輕”應(yīng)該是一根斷枝落在母親的白發(fā)上或者舌頭接觸到茫茫雪夜時的感受(比如《哀牢山》這樣的詩),而不是一根羽毛落在雪地上。前者細(xì)小但是有精神勢能,而后者則會使人產(chǎn)生精神的盲視而其影響約略為無。但是,還有一點(diǎn)必須注意的是,這種十行之內(nèi)短小的雙行體長時間寫下去的話會“打滑”的――無論是從寫作慣性、結(jié)構(gòu)、形制到抒情方式都會因?yàn)樘^于熟練而缺乏生成性、陌生感以及滯澀摩擦感。
酒,對于中國人而言。不是一種飲品,而是一個朋友。朋友分親疏遠(yuǎn)近。時酒的稱謂也很有意思。分為敬稱,比如瓊漿、玉液,還有有趣的謙稱和一般稱呼。這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尤其是外國人一不小心就會掉進(jìn)酒文化的“陷阱”。
在英文譯本中,水酒被翻譯成“watery wine”,美國人霍克斯就掉進(jìn)了中國酒文化的“陷阱”。其實(shí),水酒是謙稱,謙虛的說法,類似的還有薄酒、小酌,都是我們中國人邀請他人做客的謙稱。可絕不是說自己的酒質(zhì)量不好,往里面摻水。但是,在外國人看來,不可思議,邀請別人做客,是自己費(fèi)心費(fèi)力之事,干嗎還客氣呢?中國人歷來是重客薄己。自己寧可吃差的酒飯,也得讓客人吃好喝好。所以,當(dāng)中國人一說“略備兩三個小菜”,那就一定是場豐盛的酒宴:一說“水酒”,別以為是度數(shù)低、價錢便宜的,肯定是度數(shù)高的烈性好酒;所以,“水酒”。就如同“寒舍”、“犬子”、“拙妻”一樣,充滿了中國文化的謙虛。
在英國,有一個關(guān)于莎士比亞喝酒的傳說:莎士比亞在青少年時代海量。一次,他聽說斯特拉特福附近的畢得佛小鎮(zhèn)上的人都很能喝啤酒,就跑去要和他們較量較量。他問畢得佛鎮(zhèn)上的一個牧人:“會喝酒的在哪兒?”牧人說:“會喝酒的不在,只有能啜酒的。”兩個人一上來便痛飲啤酒,喝得昏天黑地,結(jié)果,這輕量級的人讓少年莎士比亞喝得一敗涂地。莎士比亞頭昏腦漲、步履蹣跚地離開了畢得佛鎮(zhèn)。途中,莎士比亞醉倒在路旁一株綠陰如蓋的酸蘋果樹下,后來這株樹被稱為“莎士比亞的天篷”,
在今天,酒吧里、party聚會上,人們也大多都是采用這樣的方式一醉方休,古代的中國人可不是這樣。在《紅樓夢》里,有這么一段細(xì)致地描寫了中國人喝酒的整個過程:“先是款酌慢飲。漸次談至興濃,不覺飛觥獻(xiàn)起來。當(dāng)時街坊上家家箭管。戶戶笙歌,當(dāng)頭一輪明月,飛彩凝輝。二人愈添豪興,酒到杯干。雨村此時已有七八分酒意,狂興不禁,乃對月寓懷,口占一絕云……”
面對大機(jī)器、大數(shù)據(jù)、新科技和新媒體情勢下詩歌的新變、國際化進(jìn)程的加快、集束式的詩歌生產(chǎn)、電子化的傳播以及不斷發(fā)生的熱議事件,很多寫作者、普通閱讀者和專業(yè)評論者都瞬間喪失了甄別與判斷能力。面對愈益復(fù)雜和分化的詩歌,就像盲人摸象一樣,每個人摸到的部位不同理解自然不同。相反,幾無建設(shè)性可言的自嗨、點(diǎn)贊、熱評以及長舌婦一樣的吵罵卻隨處可見。與此同時,我們又看到專業(yè)閱讀者以及“媒體批評”(包括一部分主流媒體)對詩歌的言之鑿鑿的全稱判斷。詩人的自信、自大以及膨脹的寫作心理和虛榮心已經(jīng)像霧霾一樣爆表。
一、模糊或分明的面孔:滾沸現(xiàn)場與百年游蹤
詩歌生產(chǎn)與傳播的速度、廣度和渠道的拓展以及高燒不退的社會關(guān)注度都似乎證明以往詩歌與普通受眾之間的冷漠關(guān)系已經(jīng)有所改觀。事實(shí)是如此嗎?這成了諸多專業(yè)讀者、普通讀者的共同疑問。
一年來無比火熱的詩歌活動和高分貝的造“節(jié)”運(yùn)動已亂花迷眼。有些詩歌節(jié)更像是觀光旅行團(tuán)――與地方旅游和文化資本媾和,諸多活動動輒就冠之以“國際”二字――“仿佛跨國便高出本地不只一等,卻無人檢討受邀的外賓中,有多少是真正跨得出他們自己過度的詩人?”甚至還出現(xiàn)了一些專混詩歌節(jié)卻“無詩”的專業(yè)跑場子的“詩歌節(jié)詩人”。(楊宗翰《論詩歌節(jié)如何“毀詩不倦”》)吊詭的正在于如此熱烈的詩歌現(xiàn)場和造“節(jié)”運(yùn)動中缺席的恰恰是“詩歌”和“詩性正義”。目前國內(nèi)有大大小小、五花八門的300多個詩歌獎且不斷攀升的獎金數(shù)目令人咋舌。相比較歐美等其他國家,中國的詩歌獎項(xiàng)多且亂,很多都不具備公信力。有詩人宣布今后不再領(lǐng)取國內(nèi)的任何詩歌獎(沈浩波《關(guān)于國內(nèi)的詩歌獎》)也并非刻意的自我炒作,而是有一定的針對性。
多樣化的詩歌傳播方式和出版新渠道的拓展(比如以《2017天天詩歷》《2017詩詞日歷》《親愛的日歷》《每日讀詩日歷》《給孩子讀詩》《詩光年日歷》《唐詩之美日歷》《福建詩歌周歷》《浙江詩人日歷》等為代表的詩歌日歷、周歷的激增)對詩歌社會影響度的提升是不爭的事實(shí)。詩歌與公共空間的對話(比如詩歌書店、詩歌咖啡館、詩歌主題館、詩歌走進(jìn)美術(shù)館、詩歌地鐵、詩歌巴士、詩歌船、詩歌墻等)、詩歌與其他藝術(shù)形式的跨界與融合(比如“詩意當(dāng)代”藝術(shù)融合展、“詩書本一律――現(xiàn)代詩書法展”、翟永明、韓東等人成立“十詩人電影公司”,以余秀華為主題的紀(jì)錄片《搖搖晃晃的人間》獲得第29屆阿姆斯特丹國際紀(jì)錄片電影節(jié)(IDFA)主競賽長片單元特別獎,詩電影《路邊野餐》《蝴蝶和懷孕的子彈》以及80后詩人小招(1983―2011)的紀(jì)錄片《我的希望在路上》受到關(guān)注,而以打工詩人為題材的記錄電影《我的詩篇》截至2016年12月已經(jīng)在全國180座城市通過眾籌的方式放映了900多場次)成為年度話題。詩歌對公共空間和公眾生活的介入能力正在增強(qiáng)。這似乎都在提醒人們――詩歌已經(jīng)不只是一般意義上的“回暖”“升溫”,而是“繁榮”和“一片大好”,又一個詩歌的“黃金時代”似乎已然來臨。但是,越是火熱的詩歌年代越需要沉靜下來予以反思,因?yàn)閺奈捏w特性來說詩歌的持續(xù)升溫是反常態(tài)的。炙熱的詩歌現(xiàn)場背后的深層動因、內(nèi)部機(jī)制、精神場域以及空前復(fù)雜、分層的現(xiàn)實(shí)亟待梳理、過濾、辨認(rèn)、反思。與此同時,大眾對詩歌“邊緣化”“讀不懂”的困惑以及對詩壇“個人化”“圈子化”“小眾化”的不滿仍然存在。
2016年是新詩百年誕辰――的白話詩《蝴蝶》寫于1916年。面對新詩百年,其歷史化和經(jīng)典化已經(jīng)提上日程(如各種總結(jié)性的選本《中國新詩百年志》《中國新詩百年大系?安徽卷》《安慶新文化百年 詩歌卷》《中國新詩百年百首》《百年詩經(jīng)?中國新詩300首》《中華美文?新詩讀本》《天津百年新詩》《中國新詩百年孤獨(dú)1916―2016》(西班牙語)《當(dāng)代詩經(jīng)》等,以及爭議很大的“博客中國”組織的“影響中國百年百位詩人評選”活動)。百年新詩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正在形成的自身傳統(tǒng)已是事實(shí)。著名新詩研究學(xué)者洪子誠先生則認(rèn)為百年新詩已經(jīng)取得不錯的成績,當(dāng)代的優(yōu)秀詩人已有足夠的才能參與和古典詩歌、與域外詩人的對話。
曾經(jīng)模糊的百年新詩面孔正在一次次的累積中變得越來越清晰,“在某種意義上,今天的詩歌寫作狀況正是這一百年現(xiàn)代詩實(shí)踐緩慢累積的地貌,我們無法脫離一個事物的歷史去評估它的現(xiàn)在或者預(yù)測它的未來,任何一種事態(tài)的未來都受到歷史積蓄的勢能的影響,對新詩的評價也一樣。”(耿占春《如何在茫茫詩海中濤得好詩》)新詩的動力就在于它可以有很多的方向,可以有各種各樣的嘗試,從而有諸多的可能性形態(tài)。所以當(dāng)我們面對百年新詩的時候不可能用一頂帽子去扣住它,它可能會有其他的你認(rèn)知之外的形象。
新詩與古典詩詞和外國現(xiàn)代詩的關(guān)系、新詩自身的傳統(tǒng)、一系列詩學(xué)問題以及新詩如何進(jìn)一步發(fā)展和創(chuàng)新都成為本年度不斷熱議的話題。新詩的有效性到了今天需要重新反思。中國作協(xié)詩歌委員會與江蘇省作協(xié)、揚(yáng)子江詩刊社聯(lián)合舉辦的“百年新詩論壇”就新詩的現(xiàn)代性、地方性、形式建O、譯介、少數(shù)民族詩歌創(chuàng)作、長詩等問題進(jìn)行了深入討論,對于進(jìn)一步厘清百年新詩的問題具有建設(shè)性。
新詩百年,自由、開放和創(chuàng)新一直是其發(fā)展的核心,但是其問題的癥結(jié)所在也恰恰是“新”。新詩百年之際謝冕認(rèn)為不能因?yàn)椤靶隆倍鴣G了“詩”(《中國新文學(xué):百年的憂思與夢想》)。而越來越敘事化、段子化、散文化和定型化的寫作無疑給新詩自身套上了禁閉的枷鎖,如何進(jìn)一步突破和創(chuàng)造成為當(dāng)下以及今后詩歌發(fā)展的關(guān)鍵。由蔣一談主編、北島推薦的“截句詩叢”(第一輯19種)的出版旨在重新認(rèn)識新詩的文體特性并提供新的寫作可能性,是一次美學(xué)和詩人世界觀的更新。“截句”之所以引發(fā)巨大關(guān)注和爭議正在于對“新詩”之“新”的理解以及差異。一定程度上“截句”的出現(xiàn)是重新認(rèn)識百年新詩的一個入口。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截句是名副其實(shí)的“新詩”。截句只是新詩的一端而不是異端,不能忽視和輕視寫作的可能性。一百年的中國新詩最關(guān)鍵在于一個“新”字,這并非是簡單化的文學(xué)、社會和歷史的進(jìn)化論,而是新詩代表了一種無限開放的話語方式。截句,仍然只是一種嘗試,就像當(dāng)年的一樣“自古成功在嘗試”。
二、“詩”與“歌”的分化或?qū)υ?/p>
2016年10月13日瑞典學(xué)院宣布將本年諾貝爾文學(xué)獎授予美國民謠搖滾歌手鮑勃?迪倫以表彰他“在美國歌曲的傳統(tǒng)中創(chuàng)造了新的詩性表達(dá)”。這不僅出乎太多人的意料并隨之產(chǎn)生不解、尷尬甚至憤怒,而且進(jìn)一步挑動了人們慣常意義上對詩歌邊界、文學(xué)等級的慣見,“很好,他覺得瑞典文學(xué)院的老爺子老太太們至少做了一個有趣的選擇,至少他們讓所有人也讓他自己感到尷尬――他想,你要樂于承受這種尷尬,你要試著越過界限、等級、習(xí)慣,越過那么多的深溝和回路,只有這樣的大腦才是個核桃而不是一塊鵝卵石。這是他們興致勃勃地給自己制造的問題,反正他們也聽不見來自中國的種種喧囂”(李敬澤《雜劇》)。
就漢語新詩而言,“詩”與“歌”的分化、分家或“分手”已經(jīng)很久了,而西方的搖滾樂與先鋒文化和社會運(yùn)動卻密不可分――街頭意識形態(tài)、青年亞文化、異見文化、時代精神和幽暗的體制的復(fù)雜關(guān)系,“這些作品展現(xiàn)出啟示錄般的愿景、對工業(yè)社會和現(xiàn)代科技的強(qiáng)烈反感,對官方權(quán)威和傳統(tǒng)道德的深厚敵意,以及與各種非西方的心靈與宗教傳統(tǒng)的接近。”(理查德?弗萊克斯《青年與社會變遷》)搖滾音樂代表了地下、先鋒、前衛(wèi)和頹廢以及抗議,是時代的、革命的、政治的、身體的混響。而彼岸的臺灣,一定程度上緩解詩歌與大眾的隔膜而令大眾對詩歌發(fā)生熱情的正是1970年代開始的民歌運(yùn)動。盡管從詩歌來說,鮑勃?迪倫深受蘭波、狄蘭?托馬斯和艾倫?金斯堡等詩人的影響,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并非代表了新的世界詩歌寫作標(biāo)準(zhǔn),而是一種可能性――被忽視的詩歌傳統(tǒng)。詩與歌的互動、詩教、樂教和歌詩已經(jīng)在漢語現(xiàn)代詩歌發(fā)展進(jìn)程中被規(guī)避了。業(yè)界更多關(guān)注的是詩與歌的平行和分化關(guān)系――詩歌的散文化以及對現(xiàn)代性的復(fù)雜經(jīng)驗(yàn)和智性深度的追求。對抒情性和音樂性的排斥使得詩歌成為無聲的詩和徒詩(只用于閱讀的書面文本)。而鮑勃?迪倫幫著我們重新認(rèn)識這些傳統(tǒng)――“事實(shí)上,音樂和詩是聯(lián)系著的,迪倫先生的作品異常重要地幫助我們恢復(fù)了這至關(guān)重要的聯(lián)系”(鮑勃?迪倫都被提名諾貝爾文學(xué)獎的提名信)。而從近年來詩與歌對話性的向度看,實(shí)際上一直不乏“歌詩”的傳統(tǒng)在當(dāng)下的延續(xù),比如詩人和民謠歌手合作的“十三月唱詩班”以及此前《中國新詩年鑒》的“唱響詩歌”、《人民文學(xué)》的“新樂府”、詩加歌、詩歌之王以及今年的第三屆草地詩歌音樂會、首屆成都國際詩歌音樂節(jié)、新詩百年?第十屆詩歌人間原創(chuàng)音樂會等。一些唱作人和民謠歌手、民謠詩人(張楚、潘越云、胡海泉、周云蓬、黑大春、堯十三、萬曉利、張瑋瑋、張淺潛、蘇陽、小河、小娟、莫西子詩、蔣山、洪啟、吳吞、宋雨礎(chǔ)⒙硤酢⒑瘟Α⒘醵明、趙照、鐘立風(fēng)、胡畔、王娟等)一直在做探索性的嘗試。尤其是近年的詩歌跨界傳播一定程度上將詩以歌的形式推向了大眾。12月7日,由魯迅文學(xué)院主辦的“千山靜默,萬物歌唱――詩與歌的關(guān)系研討會”就是對這一話題的深化。吉狄馬加、商震、邱華棟、李少君、郭艷、樹才、敬文東、霍俊明以及民謠歌手洪啟、馬條、鐘立風(fēng)與魯院高研班的作家、詩人們就詩與歌的話題展開討論。吉狄馬加認(rèn)為從歷史和傳統(tǒng)的向度看無論是中國還是外國詩與歌一向是很難分開的,尤其是20世紀(jì)以來國內(nèi)外一些重要詩人其詩歌影響往往是通過歌詩和演唱而與大眾聯(lián)系在一起的。因此,如何更好地推動當(dāng)下詩歌創(chuàng)作,在強(qiáng)調(diào)詩人獨(dú)立寫作的同時關(guān)注詩和歌的結(jié)合,對于今天的詩歌傳播來說作用巨大。
三、分層的詩歌與差異性的“取景框”
猶如一個巨大的體育場,擅長各種技術(shù)和項(xiàng)目的詩人運(yùn)動員正在展開各自的比拼。從詩歌類別和體式來看,現(xiàn)代詩、舊體詩詞(現(xiàn)代詩詞)、長詩(包括主題性的大型組詩)、散文詩(《我們―散文詩叢》第三輯的出版)都出現(xiàn)了共同發(fā)展的局面。從詩人身份、題材分類而言,少數(shù)民族、底層(以非專業(yè)寫作群體為主)、主旋律(比如詩刊社編選《風(fēng)景動了一下――一帶一路詩之旅 作品卷》)以及女性寫作均取得長足發(fā)展。詩歌的分層和分化狀態(tài)越來越明顯,與此相應(yīng)每一層級內(nèi)部的寫作者和詩歌狀貌同樣千差萬別,正如每個詩人手里差異性的“取景框”一樣。
舊體詩詞(現(xiàn)代詩詞)在創(chuàng)作、文獻(xiàn)整理、理論研究和多媒體傳播、對外文化交流等方面整體呈現(xiàn)出復(fù)興態(tài)勢。舊體詩詞在繼承和創(chuàng)新中力求表達(dá)新的時代經(jīng)驗(yàn),實(shí)現(xiàn)中國古典詩歌傳統(tǒng)的“當(dāng)代化”和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顯示出旺盛的活力。據(jù)統(tǒng)計,相關(guān)詩詞歌賦社團(tuán)組織達(dá)3000多個,創(chuàng)作者分布在各個社會階層和年齡段。借助于這些傳統(tǒng)的詩歌樣式,詩人更為關(guān)注的是傳統(tǒng)形式與鮮活的時代現(xiàn)實(shí)的對接,凸顯出了個人體驗(yàn)、現(xiàn)實(shí)精神以及敢于創(chuàng)新的文體求變能力。而“堅(jiān)持‘求正容變’,處理好‘新’與‘舊’、‘變’與‘不變’的關(guān)系,是詩詞寫作需要面對與破解的一個時代課題。”(蔡世平)中華詩詞學(xué)會、中華詩詞研究院、中華詩詞網(wǎng)、中國詩歌網(wǎng)、高校的詩歌研究機(jī)構(gòu)以及《詩刊》《中華詩詞》《中華辭賦》《中華詩詞研究》等刊物主辦的相關(guān)研討會、編選的作品集、研究文集、資料匯編、年度報告和理論專著均取得建設(shè)性成果,如《中華詩~發(fā)展報告》《現(xiàn)代詩詞的價值與命運(yùn)》《2017詩詞日歷》、中國詩歌網(wǎng)主辦的“新舊詩論”懇談會等。
今年是長詩的豐收年,無論是數(shù)量還是質(zhì)量都非常突出(民間設(shè)立了長詩專項(xiàng)獎“天鐸獎”),展現(xiàn)了詩人綜合寫作能力的整體提升。蕭乾父主編的《現(xiàn)代漢語史詩叢刊》歷經(jīng)十年準(zhǔn)備得以出版,收錄了1980年代以來包括海子、駱一禾在內(nèi)的42位詩人的33部長詩、11部小長詩以及1部詩學(xué)論著,共計29冊、1.4萬頁、30萬行。年度代表性的長詩文本有吉狄馬加的《致馬雅可夫斯基》、雷平陽的《去白衣寨》、陳先發(fā)的《秋興九章》、趙野的《哀歌八章》、胡弦的《蔥蘢》、姜念光的《打虎上山》、桑子的《錢江書》、樂冰的《祖宗海》、路云的《此刻,蔚藍(lán)》、張戰(zhàn)的《我,一個編號》、南子的《疑問錄》、《大風(fēng)》(曹東)、吳震寰的《孤獨(dú)者》等。這些長詩文本無論是在精神的復(fù)雜性、思想的深度、歷史的個人化、現(xiàn)實(shí)體驗(yàn)的差異性,還是在寫作技巧、修辭策略上都體現(xiàn)了一定的探索精神和實(shí)驗(yàn)意識。
第十一屆全國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創(chuàng)作“駿馬獎”的參評和獲獎詩集(朝鮮族詩人崔龍官的《崔龍官詩選集》、維吾爾族詩人伊力哈爾江?沙迪克的《云彩天花》、白族詩人何永飛的《茶馬古道記》、裕固族詩人妥清德的《風(fēng)中撿拾的草葉與月光》、彝族詩人魯娟的《好時光》)集中展示了當(dāng)下少數(shù)民族詩歌創(chuàng)作的整體成績。少數(shù)民族詩人在關(guān)注獨(dú)特的民族文化傳統(tǒng)和地方性知識的同時也更為關(guān)注現(xiàn)實(shí)生活以及個體復(fù)雜的情感,整體呈現(xiàn)出風(fēng)格各異的創(chuàng)作局面。首屆世界少數(shù)族裔文學(xué)論壇《世界少數(shù)族裔文學(xué)宣言》,旨在強(qiáng)調(diào)全球化時代少數(shù)民族的現(xiàn)狀與未來。新詩百年之際,中國作協(xié)創(chuàng)研部、中國作協(xié)詩歌委員會、中國少數(shù)民族作家學(xué)會與文聯(lián)和江蘇省作協(xié)、揚(yáng)子江詩刊社聯(lián)合舉辦“明月上林芝,新詩耀中華”少數(shù)民族詩歌創(chuàng)作研討會。本次論壇的召開是對在民族工作大會和文藝工作座談會講話中反復(fù)強(qiáng)調(diào)的民族文化融合和民族團(tuán)結(jié)的重要性精神的貫徹,也是一帶一路背景下民族文化向世界進(jìn)行展示的重要契機(jī)。與會評論家、詩人就百年來少數(shù)民族詩歌創(chuàng)作的歷史和現(xiàn)狀、民族精神、文化傳統(tǒng)、宗教民俗以及翻譯、研究和傳播都進(jìn)行了深入討論。收入310位彝族詩人《中國彝族當(dāng)代詩歌大系》(192萬字)全面展現(xiàn)了當(dāng)代彝族詩群的總體成就。《燃燒的麥穗》(夏依甫?沙拉木編選、麥麥提敏?阿卜力孜翻譯)集中展示了33位從60后到90后不同代際的維吾爾族詩人的語言和修辭的特性以及民族性、個體性、先鋒性和開放性――“真切地感受到了他們的‘新生’,因?yàn)槠湟曇耙呀?jīng)遠(yuǎn)不止于本土、地域,自身的古老傳統(tǒng),而是以世界,以當(dāng)代的詩歌思維與廣闊的文化視野來展開其寫作的。而且這個群體如此之大,其寫作的視野與水準(zhǔn),風(fēng)格的陌生與新奇,內(nèi)容上的深度與廣度,都可以與任何一個當(dāng)代民族的寫作媲美和爭雄。”(張清華《先鋒的蝙蝠把我們引向黑暗――序》)談?wù)撋贁?shù)民族詩歌往往會強(qiáng)調(diào)其地域性、民族性、異質(zhì)性以及集體無意識形成的傳統(tǒng)等,但當(dāng)下少數(shù)民族寫作同時也存在著表層、刻板、符號化的問題。一種“仿民族”“偽民俗”寫作正在興起。很多寫作者在各種場合標(biāo)舉自己的“少數(shù)”民族身份,但是他們的寫作和精神事實(shí)已經(jīng)和曾經(jīng)的歷史序列中的“少數(shù)”喪失了關(guān)聯(lián),而更多是淪為了標(biāo)簽化的“仿真”和“媚俗”性的寫作。
當(dāng)下的女性詩歌已經(jīng)不再局限于“個體”和“女性主體”,無論是在寫作風(fēng)格還是在整體格局上都呈現(xiàn)了一種“普遍性”詩學(xué)。女性詩歌在2016年呈現(xiàn)出井噴式的狀態(tài),無論是詩歌產(chǎn)量還是精神狀態(tài)。尤其大批涌現(xiàn)的年輕群體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嶄新的精神質(zhì)素和寫作方向。本年度風(fēng)格突出的女詩人詩集有《讓我背負(fù)你的憂郁》(鄭玲)、《撲朔如雪的呼吸》(王小妮)、《個人簡歷》(娜夜)、《腦電波燈塔》(童蔚)、《半島》(林雪)、《從今往后》(路也)、《我們愛過又忘記》(余秀華)、《我把自己分成碎片發(fā)給你》(西娃)、《棲真之地》(桑子)、《獵?物》(倪志娟)、《戰(zhàn)栗》(臧海英)、《樂果》(楊曉蕓)、《消失,記憶》(趙四)、《這是世界的哪里》(田暖)、《無數(shù)燈火選中的夜》(馮娜)、《大海一再后退》(顏梅玖)、《無心地看著這一切》(謝小青)、《坐在對面的愛情》(楊碧薇)、《我的降落傘壞了》(戴濰娜)、《我坐在火山的最邊緣》(包慧怡)、《蜜蜂的秘密生活》(梅依然)、《深藍(lán)》(羽微微)、《我為誘餌》(余幼幼)、《數(shù)星星的人》(玉珍)、《我熱愛過的季節(jié)》(林火火)、《草木之心》(白蘭)、《冷藏的風(fēng)景》()。
四、時感的、此刻的、物化的、碎片的詩
今年是《詩歌報》和《深圳青年報》聯(lián)合舉辦“中國詩壇1986’現(xiàn)代詩群體大展”三十周年。三十年前現(xiàn)代詩群體大展推出的64個詩歌流派以及100多個詩人的作品和大張旗鼓的宣言在無比熱鬧地助推詩歌熱潮的同時也宣告了先鋒詩歌在此后幾年的迅速冷卻、收場和隱匿。盡管耿占春認(rèn)為隨著當(dāng)年的先鋒派作家成功地轉(zhuǎn)向圖書市場、影視、學(xué)院,或走向沉寂,文學(xué)上的“先鋒派”已經(jīng)退出歷史是一個普遍的說法,但先鋒派留下來的是一種無形的先鋒精神――“文學(xué)或許不必有先鋒派,但不能失去其先鋒性,也就是一種在人類精神廣度和表現(xiàn)它的藝術(shù)形式方面的探索。”
“先鋒”“地下”顯然是當(dāng)下這個時代已經(jīng)暌違的詞,盡管偶爾被提及,但已物是人非――而酒精和搖滾樂中那些面目模糊的新時代的“披頭士”“亞文化青年”更多的時候已經(jīng)被置換成了后現(xiàn)代裝置藝術(shù)的一個碎片。新世紀(jì)以來的詩人試圖再次成為廣場上振臂一呼而應(yīng)者云集的精英或者在文學(xué)革命道路上成為馬前卒都有些近乎癡人說夢。而正是由此不堪的“先鋒”境遇出發(fā),真正的寫作者才顯得更為重要和難得。而1990年代后期以來詩歌一味的個人化、日常化,不斷地追求智性、長度、難度和現(xiàn)代性,但是其與讀者和大眾的隔膜即使在微民寫作和底層寫作的社會熱潮中也沒有消減。當(dāng)詩歌離開了詩人內(nèi)部面向更廣大的讀者群的時候,詩歌的疑問和不解就近乎鋪天蓋地。詩歌敘事性和戲劇化正在成為段子化的市儈氣、腦筋急轉(zhuǎn)彎式的口語媚俗和倫理化道德感的時代敘事。而借助社會重大主題的翻版的政治抒情詩寫作也成為一種潮流。與此同時,當(dāng)我們一再借助“底層”“草根”“打工”“賤民”“民生”談?wù)撛娙说纳鐣矸荨⒇?zé)任以及詩歌的社會性、及物性、介入現(xiàn)實(shí)的時候,卻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詩歌自身隱秘的構(gòu)造和對精神主體的持續(xù)而幽微的震動,“新詩自覺的實(shí)踐者以高度分化的語言方式,以‘原子化’的語言方式或新的‘物性論’的語言,即以一種高度分化的話語形式,處理更加微觀的感知經(jīng)驗(yàn),這是社會看不見的領(lǐng)域,似乎也無關(guān)乎社會變革、無關(guān)社會運(yùn)動,但在重構(gòu)詞與物的P系、語言與意義的關(guān)聯(lián),重塑人的感受力、進(jìn)而重新塑造人和社會的關(guān)系方面起著緩慢而隱秘的作用。”(耿占春)
六、“詩性正義”“向杜甫學(xué)習(xí)”的
困窘或可能
塔樓,樹,弱音的太陽
構(gòu)成一片霾中風(fēng)景
鳥還在奮力飛著
親人們翻檢舊時物件
記憶彎曲,長長的隧道后
故國有另一個早晨
如果一切未走向毀滅,我想
我就要重塑傳統(tǒng)和山河
――趙野《霾中風(fēng)景》
詩歌既是幽微的心靈世界的復(fù)雜呈現(xiàn),也是時代和社會主潮的揭示。“詩緣情”和“詩言志”的傳統(tǒng)構(gòu)成了詩歌發(fā)展的車之兩輪、鳥之雙翼。如果只是從詩人的責(zé)任和對公共生活介入的角度理解“詩性正義”,或者說詩人與現(xiàn)實(shí)的關(guān)系,我們都會以杜甫作為詩人的表率和榜樣。與此同時我在越來越多的詩人這里聽到了杜甫的回聲,越來越多的詩人把頭顱從西方轉(zhuǎn)回自身向傳統(tǒng)致敬。而在不同的年代,向杜甫學(xué)習(xí)、反映現(xiàn)實(shí)訓(xùn)導(dǎo)和提醒并不少見,然而我們卻在倫理化的道德論調(diào)中簡化了詩人和現(xiàn)實(shí)的關(guān)系。而當(dāng)我們必須談?wù)撛娙伺c現(xiàn)實(shí)的關(guān)系的時候,我們同樣應(yīng)該注意到杜甫是怎樣以詩歌話語的方式抒寫了一個自己的時代。比如我們可以追問,同樣是在唐朝生活的杜甫同時代的詩人,他們也深處于動蕩的社會現(xiàn)實(shí)之中,可是為什么他們沒有寫出杜甫那樣的詩歌?難道他們的詩歌與現(xiàn)實(shí)沒有關(guān)系嗎?為什么偏偏是杜甫被認(rèn)為是詩史,而他的詩歌也被視為是對一個歷史階段的最為代表性的呈現(xiàn)?由此,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詩人與現(xiàn)實(shí)的關(guān)系不是簡單地對等關(guān)系和直線型地呈現(xiàn),而是要更為復(fù)雜和值得重新思考。而杜甫的詩歌之所以能夠呈現(xiàn)出一個時代關(guān)鍵在于他對社會和世界的認(rèn)知方式始終是以詩歌美學(xué)為前提的。但是在儒家入世思想以及匡時濟(jì)世的集體心理作用之下,杜甫被我們認(rèn)可和贊許的正是體現(xiàn)了我們津津樂道的“言志載道”的詩學(xué)傳統(tǒng)。然而,杜甫的那些“緣情”的詩歌卻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nèi)被淡化和擱置了。所以,我們一直看到的是一個政治的杜甫、人民的杜甫、現(xiàn)實(shí)的杜甫和沉痛的杜甫。而這構(gòu)成的就是我們一貫以來對杜甫的刻板印象。不可否認(rèn),這一形象下杜甫的詩歌仍然是成就卓然的。然而當(dāng)我們放開眼界看看杜甫詩歌傳播的歷史,我們卻又會發(fā)現(xiàn)另外一個吊詭的事實(shí)。隨著生態(tài)壞境的堪憂,尤其是越來越多多城市被霧霾困擾,詩歌中的“生態(tài)寫作”正在深化,尤其是年底涌現(xiàn)的大量的“霧霾詩”以及網(wǎng)絡(luò)神曲《悟霾》都體現(xiàn)了詩人“介入現(xiàn)實(shí)”的努力。實(shí)際上這是詩人“生活”必然在詩中的顯影和折射――“健身器材的木椅上 / 坐著兩個老人 / 老到?jīng)]了性別 / 瞇細(xì)著眼睛 / 暖洋洋 / 曬著霾中的太陽 / 霾還很年輕 / 老人已老了很久 / 不認(rèn)識霾 / 向來,他們聽?wèi){太陽 / 不能直視的太陽和斜太陽 / 黑太陽 / 橘子太陽和典獄長太陽 / 向來 / 他們瞇著眼睛 / 他們心系太陽 / 似乎,唯如此 / 才擁有最后的 / 一絲光線的尊嚴(yán)”(宇向《老且霾》)
詩人對現(xiàn)實(shí)尤其是社會焦點(diǎn)問題和公共事件的關(guān)注從未像今天這樣強(qiáng)烈而直接。這一定程度上與媒體開放度有關(guān)。而對生存問題的揭示,對生態(tài)環(huán)境的憂慮,對民生問題的反思正印證了當(dāng)下最為流行的話――“霧霾時代詩人何為”。在敘利亞詩人阿多尼斯看來,詩歌無論是回應(yīng)現(xiàn)實(shí)還是回避現(xiàn)實(shí)都是一種“奴役”,詩歌應(yīng)該超越現(xiàn)實(shí)面向未來。這一論斷自然有其道理,但是詩人如何能夠超越現(xiàn)實(shí)和當(dāng)下而面向未來呢?詩人的寫作和“現(xiàn)實(shí)”沒有關(guān)聯(lián)嗎?顯然,記憶、現(xiàn)實(shí)和未來應(yīng)該是三位一體的,是彼此接通、相互打開的。換言之,詩歌既不能成為“現(xiàn)實(shí)”的寄生物和二手貨,也不能成為完全抽離了現(xiàn)實(shí)體驗(yàn)的空想和高蹈。由此,詩歌中的“現(xiàn)實(shí)”以及應(yīng)該具有的超拔于現(xiàn)實(shí)之外的想象能力和“修遠(yuǎn)視野”正是考察詩歌的一個入口或切口。而當(dāng)下對“詩人與現(xiàn)實(shí)”“詩歌與生活”問題的熱度不減的爭議使得寫作者對“現(xiàn)實(shí)”“現(xiàn)實(shí)感”的理解發(fā)生分歧。日常現(xiàn)實(shí)和詩歌中的現(xiàn)實(shí)是兩回事,詩人所理解的現(xiàn)實(shí)也是多層面的,任何執(zhí)于一端的“現(xiàn)實(shí)”都會導(dǎo)致偏狹或道德化的可能。正如雷平陽所提醒的不要以為有了“生活”詩歌就會迎面而來――而這是當(dāng)下詩人最容易犯的錯誤。
現(xiàn)實(shí)是分層的,每個人面對的現(xiàn)實(shí)以及相應(yīng)的感受是有差異性的,而現(xiàn)實(shí)進(jìn)入詩歌的方式更是千差萬別。而詩人如何延展、拓寬甚或再造一個語言化的現(xiàn)實(shí)是一個重要工程。尤其是在當(dāng)下“日常之詩”泛濫的情勢下,一個詩人如何在日常的面前轉(zhuǎn)到背后去看另一個迥異的空間才顯得如此重要。物象、心象和幻象必須一起在語言中賦形一個詩人,才有可能真正走在正_的路上。作為一個詩人,必須正視自我認(rèn)識和體驗(yàn)的有限,必須在詩歌中讓更多的環(huán)節(jié)來拓展自我。正如赫拉巴爾所說,站在城市的街頭,你認(rèn)識到的只是雙腳所站立的那么一丁點(diǎn)的地方,甚至對腳下城市的下水道你一無所知。而新媒體和自媒體的交互性,城市化導(dǎo)致的快速生活方式都使得當(dāng)前詩人的感受能力空前降低――大數(shù)據(jù)時代作家的感受方式也是如此的趨同化,每個人每天接受到的都是電子化的新聞化的現(xiàn)實(shí)。
七、 國際化視野與漢語詩歌“形象”
各種“全球化”視野下詩歌的跨語際、跨文化、跨國別的交流活動在2016年呈現(xiàn)繁多的局面,兩岸四地以及國際之間的詩歌活動繼續(xù)呈上揚(yáng)的態(tài)勢――比如西昌?邛海絲綢之路國際詩歌周、綏陽首屆雙河國際詩歌節(jié)、上海國際詩人節(jié)、青海國際詩人氈房會議、國際詩人揚(yáng)州瘦西湖虹橋G、首屆東亞詩人大會(中、日、韓)、第三屆國際華文詩歌獎、太平洋國際詩歌獎、2016兩岸詩會暨“桂冠詩人獎”、第十一屆“詩歌與人?國際詩歌獎”、魯迅文學(xué)院舉辦的學(xué)術(shù)論壇“黃金在天上舞蹈,命令我歌唱:詩歌的語言、翻譯和可能性”、北京語言大學(xué)主辦的“中國詩歌對外翻譯與傳播國際高層論壇”、中國詩歌學(xué)會設(shè)立中日詩歌交流辦公室并啟動《中日詩歌叢書》出版項(xiàng)目、北京師范大學(xué)國際寫作中心和磨鐵讀書會主辦的第三季詩歌翻譯坊、“胡同詩會――中外詩人面對面”“跨越語言的詩意:國際詩歌朗誦會”、上苑藝術(shù)館“國際創(chuàng)作計劃”等。除了各種國際詩歌節(jié)和交流活動之外,中國作家協(xié)會創(chuàng)研部的對外翻譯工程(含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的對外翻譯)以及中國作協(xié)詩刊社編選的《那些上緊時光的手》(一帶一路詩之旅 譯詩卷)、中國詩歌學(xué)會組織編纂的《“一帶一路”國家詩歌經(jīng)典文庫》都不斷助推詩歌翻譯尤其是漢語詩歌的對外譯介。與此同時,詩歌的國際化視野也助長了一些假想中心主義的全球化寫作幻覺。跨文化、跨語際的詩歌交流實(shí)際上并不是對等和平衡的,往往會產(chǎn)生失重的狀態(tài)――比如敘利亞詩人阿多尼斯坦誠說出的“因?yàn)槟茏x到的譯本不多,我對中國文學(xué)的認(rèn)知還是有限”。而這一不對等的關(guān)系再加之區(qū)域文化政治和不自覺的意識形態(tài)性而影響到不同國別詩人的判斷力和自信程度,“新詩是我們的傳奇。即使不使用百年新詩這樣的尺度,人們也能隱隱感覺到這一點(diǎn):新詩是漢語的現(xiàn)代傳奇。但在柏林詩歌節(jié)上,我也能強(qiáng)烈地感受到另外的情形:西方人只愿意把新詩當(dāng)成是我們的一種分類簡陋的政治文獻(xiàn)。對他們而言,新詩不過是一種文獻(xiàn)詩。”(臧棣)西川在接受《遼寧日報》訪談時也認(rèn)為中國詩人在世界上還沒有樹立起自身形象,“絕大多數(shù)詩人的作品翻譯成外文后完全處于失效狀態(tài)”。王家新則認(rèn)為許多翻譯家對新詩的建設(shè)性貢獻(xiàn)大于詩人,詩的成就與不足都與翻譯直接相關(guān)。
不斷涌現(xiàn)的以西川、王家新、陳黎、李笠、黃燦然、汪劍釗、田原、高興、樹才、李以亮、桑克、程一身、伊沙、晴朗李寒、遠(yuǎn)洋、王敖、胡續(xù)冬、周公度、周偉馳、雷武鈴、王嘎、楊鐵軍、陳太勝、舒丹丹、薛舟、倪志娟、范靜嘩、張文武、包慧怡、胡桑、王東東等為代表的“詩人翻譯家”使得詩歌譯介取得相當(dāng)大的成績。以新陸詩叢、巴別塔詩典、雅歌譯叢等為代表的詩歌翻譯工程不再是以往歐美詩歌的一統(tǒng)天下,而是向以色列、巴勒斯坦、韓國、波蘭、葡萄牙、西班牙等更多的國家和族裔拓展。2016年代表性的譯著有《里爾克詩全集》(陳寧、何家煒譯)、《英國詩歌選集》(王作良編選)、《冥想之詩》《漫游之詩》(蔡天新主編)、《帕斯捷爾納克詩選》(智量譯)、《帕斯捷爾納克傳》(王嘎譯)、《我的世紀(jì),我的野獸:曼德爾施塔姆詩選》《死于黎明:洛爾迦詩選》(王家新譯)、《寂然的狂喜:葉芝的詩與回聲》《噪音使整個世界靜默:阿米亥詩選》(傅浩譯)、《幻象集》《畢加索詩集》(余中先譯)、《舞步――邁克爾?杰克遜詩文集》(陳東飚譯)、《佩索阿詩選》(歐凡譯)、《來自巴勒斯坦的情人――達(dá)爾維什詩選》(薛慶國譯)、《蘭波詩歌全集》(葛雷、梁棟譯)、希尼的《人之鏈》(王敖譯)、《電燈光》(楊鐵軍譯)、《區(qū)線與環(huán)線》(雷武鈴譯)、《夜舞――西爾維亞?普拉斯詩選》《重建伊甸園――莎朗?W茲詩選》(遠(yuǎn)洋譯)、《高窗――菲利普?拉金詩集》(舒丹丹譯)、《奧登詩選:1948―1973》(馬鳴謙、蔡海燕譯)、《直到世界反映了靈魂最深層的需要:露易絲?格麗克詩集》(柳向陽、范靜嘩譯)、《月光的合金:露易絲?格麗克詩集》(柳向陽譯)、《卡明斯詩選》(鄒仲之譯)、《浪游者》(林克譯)、《現(xiàn)實(shí)與欲望:塞爾努達(dá)流亡前詩全集1924―1938》(汪天艾譯)、《春天 得以安葬》(高銀詩集,金丹實(shí)譯)、《密茨凱維奇詩選》(林洪亮譯)等。除了漢譯,詩歌的對外譯介也值得關(guān)注,比如多多的雙語詩集《諾言》以及古典詩歌集《獨(dú)立》、古典詩歌集和游記《尋人不遇》、痖弦的詩集《深淵》、伊路的《海中的山峰》等被翻譯成英文。此外,《中國現(xiàn)代詩系》韓語版、蔡天新《幽居之歌》亞美尼亞版、《楊克詩選》蒙古語版的出版多呈現(xiàn)了多元化的對外傳播空間的進(jìn)一步拓展。尤其是美國漢學(xué)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歷時八年之久翻譯的《杜甫詩》全譯本的出版在國外引起巨大反響。熊輝的專著《翻譯詩歌在中國的接受》、孫曉婭編選的《彼岸之觀――跨語際詩歌交流》以及日本漢學(xué)家木山英雄的《人歌人哭大旗前――時代的舊體詩》立體化呈現(xiàn)了不同視野的詩歌譯介。《人歌人哭大旗前――時代的舊體詩》以1950―70年代知識分子的舊體詩創(chuàng)作為主要研究對象,在一種相當(dāng)開闊的歷史視野中對于中國革命做出了獨(dú)到理解與別致闡釋。洪子誠認(rèn)為這本書通過對“若干熱情參加、追隨革命,卻遭受難以想象的磨難的知識分子寫的舊體詩的分析,來探索他們的獨(dú)特命運(yùn),他們不同的應(yīng)對方式和精神、心靈軌跡,并擴(kuò)大引發(fā)至對中國革命經(jīng)驗(yàn)的思考。”(《構(gòu)成了一種同一時代人的關(guān)系》)荷蘭著名漢學(xué)家柯雷(Maghiel van Crevel)的專著《精神與金錢時代的中國詩歌――從1980年代到21世紀(jì)初》則從文本、語境和原文本三個方面對1980年代中國社會文化背景、社會轉(zhuǎn)型、先鋒詩歌裂變、詩歌思潮、創(chuàng)作新變以及詩人專論進(jìn)行了別開生面、角度獨(dú)特、立論新穎的觀察、剖析與反思,體現(xiàn)了一個“局外人”對中國當(dāng)代詩壇“多方面的深入而獨(dú)到的觀察、理解”。陳太勝翻譯的特里?伊格爾頓的《如何讀詩》則向我們敞開了詩歌閱讀的多重空間和可行性方法。
一定程度上,漢語詩人在國際上獲獎也是漢語詩歌寫作認(rèn)可度的提升,比如吉狄馬加獲得2016年度歐洲詩歌與藝術(shù)“荷馬獎”以及羅馬尼亞《當(dāng)代人》雜志與布加勒斯特作家協(xié)會聯(lián)合授予的“卓越詩歌獎”和“詩歌創(chuàng)作獎”、中國臺灣詩人楊牧獲得瑞典“蟬獎”、多多獲得墨西哥“新黃金時代詩歌獎”、瀟瀟獲得羅馬尼亞作家協(xié)會頒發(fā)的“阿爾蓋齊詩歌獎”。
本年內(nèi)詩歌批評與研究繼續(xù)深化,研究者的整體考察和問題意識突出。尤其是在新詩百年之際相關(guān)的研討會、研究文集、報告和文叢、專著均取得建設(shè)性成果。代表性的有《二十世紀(jì)中國新詩理論史》《中國現(xiàn)代詩學(xué)叢書》(12種)《聲音的詩學(xué):現(xiàn)代詩抒情藝術(shù)研究》《李瑛詩歌研究文選》《大詩論――中國當(dāng)代詩歌批評年編2014―2015》《新世紀(jì)詩歌批評文選》《詩的證詞――一帶一路詩之旅 詩學(xué)卷》《70后批評家文叢》《閱讀的姿勢》《梁平詩歌研究》《分叉的想象》《螢火時代的閃電》《陌生人的懸崖》《在巨冰傾斜的大地上行走――陳超和他的詩歌時代》《讀一首詩,讓時光安靜》(文本細(xì)讀)等等。李少君、劉復(fù)生主編的《二十一世紀(jì)的中國詩歌》收錄了17篇關(guān)于新世紀(jì)以來的詩歌現(xiàn)象和問題研究文章,涉及到詩歌的地方性、現(xiàn)實(shí)感、校園詩歌、詩歌的大眾化、詩歌倫理以及傳播等問題。

預(yù)計1個月內(nèi)審稿 部級期刊
中國青年發(fā)展基金會主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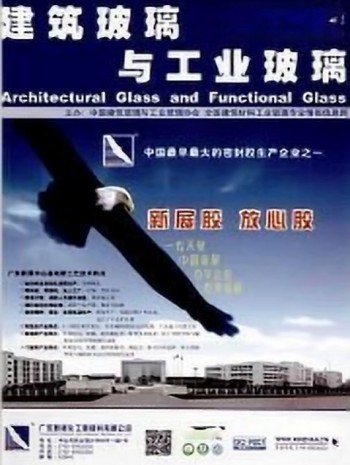
預(yù)計1個月內(nèi)審稿 省級期刊
中國建筑玻璃與工業(yè)玻璃協(xié)會;建筑材料工業(yè)技術(shù)情報研究所主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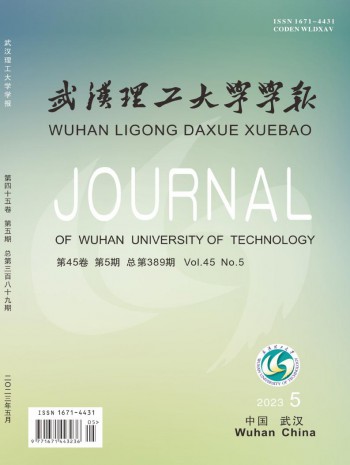
預(yù)計1個月內(nèi)審稿 部級期刊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主辦

預(yù)計1個月內(nèi)審稿 省級期刊
福建省市場監(jiān)督管理局主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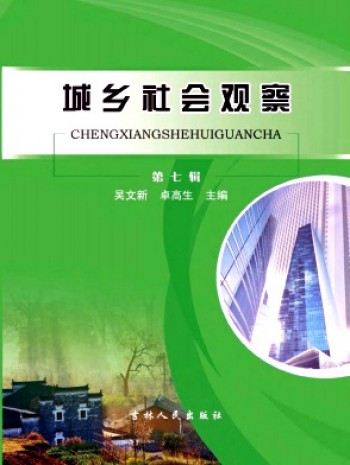
預(yù)計1個月內(nèi)審稿 省級期刊
山東大學(xué)(威海)哲學(xué)與社會發(fā)展研究中心;溫州大學(xué)馬克思主義學(xué)院主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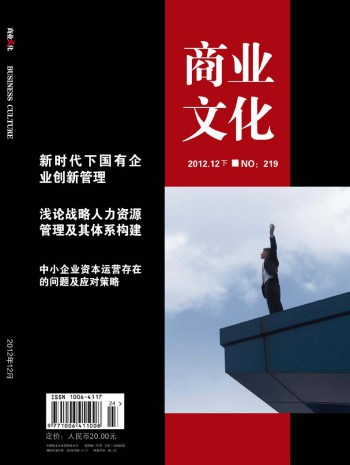
預(yù)計1個月內(nèi)審稿 部級期刊
中國商業(yè)聯(lián)合會主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