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shí)間:2023-03-14 15:18:52
引言:易發(fā)表網(wǎng)憑借豐富的文秘實(shí)踐,為您精心挑選了九篇現(xiàn)代主義繪畫(huà)論文范例。如需獲取更多原創(chuàng)內(nèi)容,可隨時(shí)聯(lián)系我們的客服老師。

摘 要:本文通過(guò)對(duì)兒童藝術(shù)特點(diǎn)的剖析,揭示西方現(xiàn)代主義繪畫(huà)吸收和借鑒兒童藝術(shù)造型符號(hào)之后所形成的前所未有的率真、稚拙和清新的品質(zhì),并結(jié)合藝術(shù)家的具體作品分析進(jìn)一步指出西方現(xiàn)代主義繪畫(huà)在本質(zhì)上有別于兒童稚拙藝術(shù),張揚(yáng)著獨(dú)特的藝術(shù)個(gè)性,具有大巧若拙,拙中藏巧的藝術(shù)境界。
一、引 言
人們過(guò)去并未意識(shí)到兒童隨意而愉快的涂抹有什么特殊意義,更談不上對(duì)兒童藝術(shù)的發(fā)現(xiàn)及關(guān)注,然而,隨著人類藝術(shù)史上對(duì)兒童藝術(shù)的發(fā)現(xiàn)及現(xiàn)代藝術(shù)的產(chǎn)生,兒童藝術(shù)在當(dāng)代藝術(shù)世界的位置正日益凸顯。現(xiàn)在,“兒童藝術(shù)”已是被普遍接受的概念,兒童藝術(shù)中那種形象的簡(jiǎn)化、畫(huà)面的和諧、富有表現(xiàn)力的線條、大膽的純色平涂以及那種無(wú)意識(shí)的創(chuàng)作狀態(tài),使得西方現(xiàn)代藝術(shù)家懷著新奇的目光從兒童藝術(shù)中汲取營(yíng)養(yǎng)。
二、西方現(xiàn)代主義藝術(shù)大師對(duì)兒童藝術(shù)的認(rèn)識(shí)與評(píng)價(jià)
兒童的作品究竟有何魅力?為什么會(huì)吸引全世界藝術(shù)家的目光?在兒童藝術(shù)中,兒童常常以其天真率直的心態(tài)每每使我們拍手稱快,是任何人為的方法都無(wú)法企及的。兒童藝術(shù)是無(wú)意識(shí)下創(chuàng)作的作品,是兒童心智和心緒的自然流露,往往呈現(xiàn)著藝術(shù)創(chuàng)作最初的也是最純粹的源泉。其構(gòu)圖造型稚拙有趣,似無(wú)法之法,有意想不到的生動(dòng)。正如黑格爾所說(shuō):“兒童是最美好的,一切個(gè)別特殊性在他們身上好像都還沉睡在未展開(kāi)的幼芽里,還沒(méi)有什么狹隘的東西在他們的胸中激動(dòng),在兒童還在變化的面貌上,還看不出承認(rèn)繁復(fù)意圖所造成的煩惱,因而在兒童繪畫(huà)里表現(xiàn)出來(lái)的是他們對(duì)事物無(wú)意識(shí)的、天真率直的看法。133229.cOm”兒童藝術(shù)更具創(chuàng)造性和表現(xiàn)性,注重個(gè)人感受。兒童天性充滿熱情,能主動(dòng)、自由地表現(xiàn)畫(huà)面,兒童看世界有他們自己的獨(dú)特眼光,他看起人來(lái),只看到一個(gè)人的一個(gè)大頭,頭上的兩只眼睛,一個(gè)鼻子,一張嘴巴,什么耳朵、頭發(fā)、眉毛,他都沒(méi)有看見(jiàn),所以他不畫(huà)一個(gè)人的身體,他看得不重要,只畫(huà)一條線來(lái)表示。這些入眼的觀察對(duì)象在兒童的心目中形象分外鮮明。兒童是畫(huà)其所想而非畫(huà)其所見(jiàn),因此兒童畫(huà)出的作品往往想象豐富,用色大膽,富有生氣,有更多的靈性。西方現(xiàn)代派藝術(shù)中,反叛傳統(tǒng),追求單純和質(zhì)樸無(wú)華是其共同的目的和重要特征,因此,現(xiàn)代藝術(shù)家們不約而同地將目光投向了兒童藝術(shù),而且給予兒童藝術(shù)以高度的評(píng)價(jià),甚至對(duì)兒童的藝術(shù)狀態(tài)和兒童的藝術(shù)作品崇拜不已。現(xiàn)代藝術(shù)大師畢加索曾說(shuō)過(guò):“我曾經(jīng)能像拉斐爾那樣作畫(huà),但我卻花了畢生的時(shí)間去學(xué)會(huì)像兒童那樣作畫(huà)。”這在當(dāng)時(shí)是很有代表性的。其實(shí)這種對(duì)兒童藝術(shù)的新的認(rèn)識(shí)和評(píng)價(jià)在野獸派那里已有所表現(xiàn)。康定斯基崇拜兒童藝術(shù)是因?yàn)樗J(rèn)為兒童藝術(shù)是對(duì)事物內(nèi)在本質(zhì)的直覺(jué)表現(xiàn),他說(shuō):“兒童除了描摹外觀的能力之外,還有力量使永久的內(nèi)在真理處在它最能有力地得以表現(xiàn)的形式中。……兒童有一種巨大的無(wú)意識(shí)力量,它在此表達(dá)自身,并且使兒童的作品達(dá)到與成人一樣高(甚至更高)的水平。”畫(huà)家馬蒂斯、杜飛、夏加爾,尤其是克利、米羅和杜布菲等,同樣感到了兒童藝術(shù)的魅力。西方藝術(shù)家所向往的那種無(wú)意識(shí)的創(chuàng)作狀態(tài)、“信手涂抹”在兒童藝術(shù)那里得到了很好的詮釋。
三、西方現(xiàn)代主義繪畫(huà)對(duì)兒童藝術(shù)的借鑒與模仿
從19世紀(jì)后半葉起,西方畫(huà)壇發(fā)生了重大變化,眼花繚亂的西方現(xiàn)代畫(huà)派,既受到兒童繪畫(huà)在藝術(shù)形式上以及表現(xiàn)技巧方面的啟發(fā),更受到兒童對(duì)待繪畫(huà)的基本態(tài)度無(wú)意識(shí)的強(qiáng)烈沖擊。對(duì)兒童藝術(shù)的推崇與模仿直接反映在他們作品的形式中。克利就一直崇拜兒童的這種天真狀態(tài),并以自己的方式加以模仿。克利在繪畫(huà)技巧上使用兒童那種環(huán)繞的、粗陋的輪廓線,反應(yīng)在作品《動(dòng)物園》、《他喊叫,我們玩》和《女舞蹈家》中,這些畫(huà)中線條技法與兒童素描的線條技巧很接近,盡管它更細(xì)窄,更優(yōu)美。《高架橋的革命》畫(huà)面上簡(jiǎn)單的甚至笨拙的高架橋,表現(xiàn)出了克利對(duì)兒童畫(huà)天真稚拙的形象以及符號(hào)化形象的興趣。在米羅的繪畫(huà)世界中同樣可以感受到這位大師對(duì)兒童藝術(shù)的推崇,在他1948年至1953年的許多繪畫(huà)作品中,人物沒(méi)有身體表現(xiàn),頭部直接安在以球形腳為末端的直腿上,整個(gè)臉像一個(gè)不規(guī)則的橢圓形或圓形,這種極端單純化的形象的變體,也就是兒童畫(huà)中的“蝌蚪人”樣式,如作品《在甲殼下部》、《黎明時(shí)瞪羚的哭叫》和《繪畫(huà)》以及早期最有名的作品《農(nóng)場(chǎng)》都已呈現(xiàn)出一種兒童般稚拙的風(fēng)格傾向。后來(lái)由于戰(zhàn)爭(zhēng),米羅的作品表現(xiàn)出前所未有的恐怖之感,但畫(huà)面依然保持他那種天真、優(yōu)美的風(fēng)格。如系列《星座》及《女詩(shī)人》都是在戰(zhàn)爭(zhēng)的威脅之下創(chuàng)作出來(lái)的,但我們從中看不到任何血腥的痕跡。無(wú)怪乎有批評(píng)家說(shuō):“米羅的天才是一種返老還童的天才。”涂鴉和兒童藝術(shù)也是杜布菲的范例和靈感來(lái)源,他特別贊同用最簡(jiǎn)單的正面和側(cè)面形象及兒童的輪廓線風(fēng)格畫(huà)出大腦袋粗陋人物,也贊同兒童對(duì)記憶中傳達(dá)信息的細(xì)節(jié)的強(qiáng)調(diào),杜布菲甚至希望以更加粗蠻、直接和確定的方式拋棄“后天學(xué)到的手段”,去探討一條回到“藝術(shù)基本的、形成的時(shí)期,記錄下兒童式的天真與好奇狀態(tài)的道路”。在他早期的作品中,如《街上的男人》畫(huà)面中描繪的是巴黎的景色與生活,具有一種天真稚拙的趣味。此后,他很快擺脫了克利藝術(shù)中那種幻想、略顯天真的氣質(zhì),而轉(zhuǎn)向一種獨(dú)特的、奠定自己在藝術(shù)史上地位的繪畫(huà)創(chuàng)作方法,創(chuàng)作出一些涂鴉形態(tài)的作品,如在《人間的聯(lián)歡節(jié)上》,我們可以看到的一種以此法創(chuàng)作出來(lái)的令人厭惡和不安的歡樂(lè)氛圍。
西方現(xiàn)代派藝術(shù)中的荒誕和隨意性與兒童藝術(shù)中的荒誕和隨意是一致的。“荒誕藝術(shù)比起優(yōu)美、崇高的藝術(shù)更加深刻地表現(xiàn)了人之所以為人的內(nèi)在生命力。”這是西方現(xiàn)代畫(huà)派對(duì)怪誕藝術(shù)的看法和推崇。現(xiàn)代派大師馬蒂斯、畢加索等人就從古代非洲的繪畫(huà)和雕塑中吸取怪異而又荒誕的特點(diǎn),在我們的眼中極不符合常規(guī),但這與兒童美術(shù)中的無(wú)意識(shí)荒誕的想法極為相似。西方現(xiàn)代主義繪畫(huà)對(duì)兒童藝術(shù)的接受主要表現(xiàn)在欣賞他們的天然和單純,使得他們的作品具有稚拙的面貌,法國(guó)評(píng)論家在觀看他們的畫(huà)展時(shí),曾稱這些顏色不符合“客觀實(shí)際”,藝術(shù)形象難以理解。雖說(shuō)在現(xiàn)在看來(lái)有點(diǎn)言過(guò)其實(shí),然而的確在馬蒂斯等人的作品中反映出畫(huà)家進(jìn)一步轉(zhuǎn)向表現(xiàn)內(nèi)心情感,這也是近現(xiàn)代以來(lái)西方繪畫(huà)逐漸擺脫傳統(tǒng)上摹寫(xiě)現(xiàn)實(shí)的主流畫(huà)法的新的一步,在野獸派繪畫(huà)中,馬蒂斯等畫(huà)家的一些人物畫(huà)有一個(gè)特點(diǎn),人物的形象往往有彎曲的形態(tài)和封閉的輪廓線。如馬蒂斯的《浴者》和《海濱婦女》,這些作品使人想起兒童藝術(shù)的某些特點(diǎn),人物的形象看起來(lái)“不準(zhǔn)確”。上述這些對(duì)兒童藝術(shù)語(yǔ)言的模仿甚至直接挪用只是一個(gè)方面,更重要的是現(xiàn)代藝術(shù)家們從兒童那里重新獲得天真、純樸和清新的內(nèi)在品質(zhì)。
四、現(xiàn)代主義繪畫(huà)大巧若拙
現(xiàn)代主義繪畫(huà)在許多方面更借鑒兒童藝術(shù),但他們的目的并非簡(jiǎn)單地重創(chuàng)兒童繪畫(huà),在技巧、表現(xiàn)形式上與兒童繪畫(huà)有很大差別。兒童繪畫(huà)是在生命之初對(duì)世界的探索嘗試,表達(dá)的是整個(gè)生命尚未展開(kāi)的天性。而大師的繪畫(huà)則是在生命成熟階段對(duì)探索世界的提煉總結(jié),表達(dá)出整個(gè)生命發(fā)展過(guò)程凝結(jié)出來(lái)的人格特征和藝術(shù)個(gè)性。所以,兒童畫(huà)一張張來(lái)看,大不相同,而大面積看起來(lái),其面貌給人的感覺(jué)大同小異。大師繪畫(huà)則不同,都具有獨(dú)一無(wú)二性。克利、米羅和杜布菲等現(xiàn)代畫(huà)家在對(duì)兒童藝術(shù)的借鑒中充分展示了各自的藝術(shù)個(gè)性,他們使用兒童的符號(hào)和技法也并非偶然,而是他們比其他藝術(shù)家更需要這種敏銳的感覺(jué)力,帶著激情去感受兒童的繪畫(huà)世界。他們的繪畫(huà)有著精致的層次和精湛的技巧,雖然繪畫(huà)的最終效果有著明顯的隨意性,但與兒童天真的藝術(shù)并未完全融合,保持著各自的獨(dú)立性,又相得益彰。兒童的繪畫(huà)作品是“原始”形態(tài)的、天真純樸的,而又往往以“稚拙”的樣式表現(xiàn)出來(lái)。這在兒童是很可貴的,也是許多中外畫(huà)家所追求的藝術(shù)境界。那么藝術(shù)家追求的天真純樸和稚拙與兒童繪畫(huà)所表現(xiàn)出的天真純樸和稚拙是否如出一轍呢?這對(duì)于我們更深一步了解兒童藝術(shù)是至關(guān)重要的。審美創(chuàng)造一般都是由拙到巧、再由巧返拙的階段。開(kāi)始之拙,是生疏幼稚的真拙,隨著審美創(chuàng)造技巧的提高,進(jìn)入精巧工巧階段,有了豐富的經(jīng)驗(yàn)、功夫、素養(yǎng),才能落盡繁華歸于樸淡,進(jìn)入大巧若拙的境界。沒(méi)有深厚的功底,片面為拙而拙,只會(huì)粗陋低俗。戴復(fù)古說(shuō):“樸拙唯宜怕近村。”(《論詩(shī)十絕》)即使是巧后之拙,如果刻意追求拙的外在形式,則是一種造作,失去其真正的天然本質(zhì)。拙樸絕非粗率平庸之輩所能達(dá)到的,它是審美創(chuàng)造高度成熟的標(biāo)志。追求兒童趣味的藝術(shù)家在某些方面與兒童繪畫(huà)較為相似,例如:以線為主,平涂色彩,不講焦點(diǎn)透視及夸張變形手法等等。但兒童藝術(shù)中的那種天真稚拙的情趣被藝術(shù)家們加以發(fā)揮、拓展,成為嶄新的藝術(shù)形式。雖然他們畫(huà)中的“拙”與兒童繪畫(huà)中的“拙”有著形式上的相似,但卻又有著本質(zhì)的區(qū)別:他們是老子所說(shuō)的“大巧若拙”之“拙”。寫(xiě)意大師崔子范也曾說(shuō):“一個(gè)沒(méi)有受過(guò)專業(yè)訓(xùn)練的孩子只憑熱情作畫(huà)。在他長(zhǎng)大之后,也應(yīng)該注意使自己回到童年的心態(tài),去重新發(fā)掘自己兒時(shí)的天性——自由地而不是造作地在畫(huà)中表現(xiàn)自己的感情。當(dāng)一個(gè)成熟的畫(huà)家運(yùn)用這種方式作畫(huà)時(shí),當(dāng)他將藝術(shù)大師的精湛技巧與孩子般的天真爛漫融合在一起時(shí),會(huì)感到極大的快慰。”雖然西方的克利、米羅和杜布菲等畫(huà)家的作品源于兒童繪畫(huà)的造型符號(hào),但他們靠熟練精深的技巧來(lái)完成。大體上都經(jīng)歷了由開(kāi)始的不成熟,到技法日趨精深,進(jìn)而追求“返璞歸真”的過(guò)程。雖然也有追求兒童“拙味”的畫(huà)家未經(jīng)過(guò)專門的訓(xùn)練,但他們也難免經(jīng)受藝術(shù)傳統(tǒng)的熏陶,前輩及同代畫(huà)家的影響與個(gè)人技巧的錘煉。克利雖曾說(shuō):“無(wú)需什么技巧”,但他畢竟經(jīng)過(guò)了傳統(tǒng)藝術(shù)熏陶,其藝術(shù)風(fēng)格必有傳統(tǒng)技巧的痕跡。可見(jiàn)兒童的稚拙是幼稚的拙,而畫(huà)家的稚拙是“拙中藏巧”之拙。“拙樸最難,拙近天真,樸近自然,能拙樸則渾厚不流為滯膩。”拙樸之拙,是大巧,不露痕跡,使人不覺(jué)其巧。它是“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shí)濃”(《東坡題跋》),在平實(shí)樸素粗散的形式中,蘊(yùn)含著深厚的審美素養(yǎng)和豐富的情感意味。沒(méi)有一定技巧的錘煉,一味片面追求兒童“拙味”,只會(huì)流于粗俗淺薄,達(dá)不到自然渾化的拙樸之境。
五、結(jié) 語(yǔ)
總之,現(xiàn)代藝術(shù)家們從兒童藝術(shù)中獲取到了造型符號(hào)的靈感,同時(shí)也通過(guò)自己的作品和言論促成了人們對(duì)兒童藝術(shù)的進(jìn)一步關(guān)注、承認(rèn)和了解。在現(xiàn)代藝術(shù)中,傳統(tǒng)的審美標(biāo)準(zhǔn)首先被打破,幾乎沒(méi)有什么尺度可以將兒童藝術(shù)與大師的作品相區(qū)別。當(dāng)然,西方現(xiàn)代主義藝術(shù)家的作品與兒童的繪畫(huà)作品之間的相仿程度,也不能真正完全劃上等號(hào),這些現(xiàn)代藝術(shù)大師的繪畫(huà)畢竟是落盡繁華歸于樸淡,大巧若拙,拙中藏巧。
參考文獻(xiàn):
[1] 羅伯特·戈德沃特.現(xiàn)代藝術(shù)中的原始主義[m].殷泓譯.南京:江蘇美術(shù)出版社1993:54.
[2] 阿恩海姆.藝術(shù)與視知覺(jué)[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3] 崔慶忠.現(xiàn)代美術(shù)史話[m].北京: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2001.
論文關(guān)鍵詞:傳統(tǒng)審美 現(xiàn)代美術(shù) 沖突
論文摘要:中國(guó)傳統(tǒng)藝術(shù)在歷史的歲月中沉積了千年的精華散發(fā)出特有的氣質(zhì)和沁人心脾的馥香。現(xiàn)代藝術(shù)在審美實(shí)踐的意義上,不僅在自身內(nèi)部激化出前所未有的話語(yǔ)形式,而當(dāng)代藝術(shù)對(duì)傳統(tǒng)審美理想的顛覆沖突愈明顯。下面筆者試從三方面論述中國(guó)傳統(tǒng)審美與現(xiàn)代美術(shù)的沖突
一、審美思維方式的沖突
傳統(tǒng)的審美理想在思維方式方面上,注重萬(wàn)物的聯(lián)系和感性自覺(jué)的心理體驗(yàn)。這種思維方式中沒(méi)有把大千世界看成是獨(dú)立于人以外的純粹客體中國(guó)傳統(tǒng)審美理想體現(xiàn)一種宏觀整體的審美思維方式,藝術(shù)講求心靈的物化,又是物的情話,心物合一超以象外。老子云:“塞其兌,閉其門”就是清除心靈的塵灰,保持內(nèi)心的最大虛空、靜寂,直觀體悟世界萬(wàn)物“和其光,同起塵”達(dá)到“玄同”的藝術(shù)理想。同時(shí)這種思維方式有著虛空靈動(dòng),就是傳統(tǒng)審美中的神韻、飄逸、超拔、高逸、虛清等。所以在傳統(tǒng)中國(guó)畫(huà)中講求“氣韻生動(dòng)”、 “妙在能會(huì)、神在能離”等一種格調(diào)清高的審美追求。
現(xiàn)代美術(shù)與傳統(tǒng)審美思維的沖突體現(xiàn)在兩方面。首先,現(xiàn)代美術(shù)缺乏主體內(nèi)心的自省,取而代之的是西方人文藝復(fù)興以來(lái)的人文主義思潮,即以人性對(duì)抗神性、以人權(quán)反對(duì)神權(quán),以人為中心的思維傾向。兩者都是以“人”為中心,但兩者的審美思維方向有質(zhì)的差異。中國(guó)傳統(tǒng)審美思維方式強(qiáng)調(diào)虛靜、心靈自由以及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關(guān)系。現(xiàn)代美術(shù)在藝術(shù)思維上強(qiáng)調(diào)人的自然屬性和社會(huì)屬性,顯示為人對(duì)自然的征服力、控制力,人于自然產(chǎn)生一種外離對(duì)抗性。在一定的社會(huì)時(shí)代中以人性對(duì)抗神性、以人權(quán)反對(duì)神權(quán)、體現(xiàn)出了人類意識(shí)的覺(jué)醒有進(jìn)步性。其次,現(xiàn)代美術(shù)思維方式中缺乏傳統(tǒng)審美宏觀整體性,現(xiàn)代美術(shù)多用類似解構(gòu)主義的思維方式,肢解、分割使主體思維獨(dú)立單一。
二、審美價(jià)值取向的沖突
傳統(tǒng)審美理想的價(jià)值取向,重交感,重人生。首先“交感”就是“天人合一”的動(dòng)態(tài)過(guò)程,也就是萬(wàn)物生命的發(fā)生過(guò)程。按《周易》的觀念,整個(gè)宇宙是陰,陽(yáng)兩種元素交感而成的動(dòng)態(tài)過(guò)程。西漢董仲舒的天人感應(yīng)說(shuō)、宋明理學(xué)家主張的天人相通都是在審美取向上重交感。再次“重人生”源于“交感”的基礎(chǔ)。周敦頤說(shuō)“二氣交感,化生萬(wàn)物”。 就是把人看作萬(wàn)物之靈,天地之德,天地之心。即以人的生命活動(dòng)為內(nèi)在機(jī)制的宇宙一體化,天地萬(wàn)物看作統(tǒng)一生命系統(tǒng)。中國(guó)古人是以這種對(duì)自然的特殊情感和內(nèi)求自省的方法完成美的理想追求。傳統(tǒng)中國(guó)畫(huà)家在對(duì)大自然領(lǐng)悟人生,借物寓意,予以揮毫把無(wú)情之物變成有情之物。現(xiàn)在我們還能從他們畫(huà)的頑石中感受到“雪盡身還瘦,云生勢(shì)不孤”的氣概;從山林中感受“春山澹治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凈而如妝,冬山慘淡而如睡”的情態(tài)。
現(xiàn)代美術(shù)中這種“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的審美價(jià)值取向很少了。現(xiàn)代美術(shù)審美取向傾向于個(gè)人自我價(jià)值、自然價(jià)值、社會(huì)價(jià)值分離,強(qiáng)調(diào)主體對(duì)社會(huì)對(duì)人生的悲觀消極或厭惡不滿發(fā)泄的態(tài)度。現(xiàn)代美術(shù)價(jià)值取向其實(shí)是自身內(nèi)部激化出前所未有的話語(yǔ)形式,突顯當(dāng)代審美文化所面臨的困惑。
三、藝術(shù)表現(xiàn)形式的沖突
傳統(tǒng)中國(guó)畫(huà)的藝術(shù)表現(xiàn)形式只在筆墨之間唱吟畫(huà)家心聲,簡(jiǎn)單而單純的黑白水墨卻孕育著中國(guó)文化之精華。
第一、以水墨為上。故有墨從筆出,筆以墨顯,筆取其氣,墨取其韻。中國(guó)古人將自己實(shí)踐經(jīng)驗(yàn)和精神追求集中于此,其作品中的造型符號(hào)融哲理、藝術(shù)、人生一體,體現(xiàn)儒道佛三家哲理。第二、重意忘形。“畫(huà)之當(dāng)意寫(xiě),不在形似耳”【《元·湯垕》畫(huà)鑒畫(huà)論】,縱觀中國(guó)美術(shù)史,除徐渭、、石濤等大寫(xiě)意畫(huà)家不論,即便是工筆畫(huà):山水、人物、花鳥(niǎo)也不是單純的模擬,刻意酷似,而是“畫(huà)見(jiàn)其大意,而不為刻畫(huà)之跡”【《林泉高致·山水訓(xùn)》】。
中國(guó)傳統(tǒng)繪畫(huà)重物象的內(nèi)在體態(tài)、氣韻、生命神采。西方繪畫(huà)則重寫(xiě)實(shí)性,藝術(shù)形式追求逼真,強(qiáng)調(diào)對(duì)事物科學(xué)精確的刻畫(huà)。印象派的出現(xiàn)是現(xiàn)代藝術(shù)的里程碑。在一定程度上印象派否定了西方傳統(tǒng)的單一的藝術(shù)表現(xiàn)形式,放棄了原有嚴(yán)謹(jǐn)?shù)脑煨湍芰ΑC佬g(shù)開(kāi)始分門別派,藝術(shù)表現(xiàn)形式也愈加豐富。“現(xiàn)代派藝術(shù)之父”塞尚,他不再重客觀事物的模仿而注入永恒的形體結(jié)構(gòu);還有梵高,他用明亮灼熱的色彩、奔放顫動(dòng)的曲線傳達(dá)激動(dòng)熾熱的心身。從印象派到野獸派、表現(xiàn)主義、立體主義、超現(xiàn)實(shí)主義、抽象主義……這些現(xiàn)代主義美術(shù)豐富了原有的藝術(shù)表現(xiàn)形式,給人以全新的藝術(shù)震撼,為人類文化作出了巨大貢獻(xiàn)。但西方的文化藝術(shù)有著他們本身民族文化發(fā)展的軌跡。如果一味仿照其表現(xiàn)形式,牽強(qiáng)附會(huì)、打著復(fù)興中國(guó)藝術(shù)的旗號(hào)卻是在毀滅中國(guó)藝術(shù)之靈魂和生命。
綜上所述,當(dāng)今世界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交流廣泛,一方面使我們的藝術(shù)發(fā)展更多元化,另一方面一些現(xiàn)代藝術(shù)家盲目臣服于西方現(xiàn)代、后現(xiàn)代主義藝術(shù)的繪畫(huà)方式。伴隨著的是美術(shù)價(jià)值的空洞性、虛無(wú)性,一些現(xiàn)代藝術(shù)與傳統(tǒng)審美理想相去甚遠(yuǎn)。
摘要 本文對(duì)傅抱石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和藝術(shù)實(shí)踐進(jìn)行考察,通過(guò)對(duì)其個(gè)人經(jīng)歷、藝術(shù)創(chuàng)作及理論的分析,比較他在吸收傳統(tǒng)中的不同之處,以展示其對(duì)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在新時(shí)代變革中的重要貢獻(xiàn)。通過(guò)對(duì)他的理論實(shí)踐與繪畫(huà)創(chuàng)作進(jìn)行研究,能給我們今天的藝術(shù)創(chuàng)新有益的啟示。
關(guān)鍵詞:傅抱石 傳統(tǒng) 變革
中圖分類號(hào):J519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中國(guó)在20世紀(jì)上半期,正處于國(guó)家危難之時(shí),藝術(shù)面臨的境地也是如此。藝術(shù)在西方文化沖擊和傳統(tǒng)文化流失的夾縫中生存,此時(shí)藝術(shù)家一方面積極地救亡圖存,另一方面投身于藝術(shù)。傅抱石這位20世紀(jì)藝術(shù)理論巨匠和中國(guó)畫(huà)大師,恰好生活在這個(gè)時(shí)候,在國(guó)難與藝術(shù)生存危機(jī)之中,他對(duì)中國(guó)古代藝術(shù)傳統(tǒng)理論進(jìn)行了探尋、研究,并借鑒日本研究成果,發(fā)展了自己的理論體系。
一 學(xué)貫古今,貯備深厚文化功力
傅抱石從小家庭非常貧困,很小就沒(méi)有了父親,在好心人資助下求學(xué),以優(yōu)異成績(jī)畢業(yè)并任教于師范專科學(xué)校,在此時(shí)期,他利用業(yè)余時(shí)間完成一本10萬(wàn)字的《繪畫(huà)源流述概》,當(dāng)時(shí)年僅21歲。
1933年,傅抱石在徐悲鴻的舉薦下到日本留學(xué)。在此期間,日本學(xué)者伊勢(shì)專一郎于昭和8年刊行了《自顧愷之到荊浩支那山水畫(huà)史》一書(shū),日本學(xué)界對(duì)此書(shū)大力追捧。經(jīng)過(guò)認(rèn)真研讀,傅抱石從中發(fā)現(xiàn)了諸多的錯(cuò)誤,于是寫(xiě)了《論顧愷之至荊浩之山水畫(huà)史問(wèn)題》,對(duì)伊氏的錯(cuò)誤進(jìn)行一一的指正。回國(guó)以后,他在此基礎(chǔ)上進(jìn)一步深入研究,先后作了《六朝時(shí)代之繪畫(huà)》、《中國(guó)古代山水畫(huà)史的研究》等溫。
在《中國(guó)古代山水畫(huà)史的研究》中針對(duì)日本學(xué)者對(duì)中國(guó)文字?jǐn)嗑涞那啡保瑢?duì)顧愷之的《畫(huà)云臺(tái)山記》重新作了文字校訂。傅抱石在《壬午重慶畫(huà)展自序》中說(shuō):“近十年來(lái),可說(shuō)十分之七的時(shí)間用在美術(shù)史、畫(huà)史,和畫(huà)論的考察,很少時(shí)間握筆作畫(huà)。”作畫(huà)可以說(shuō)成了他的業(yè)余活動(dòng),然而他最終卻成了獨(dú)領(lǐng)一代的大畫(huà)家,個(gè)中原由正如陳傳席分析的:“傅抱石的繪畫(huà)之成功,有很多因素。其中有一點(diǎn)要注意,就是他精通美術(shù)史。”由此可以說(shuō)明,他對(duì)中國(guó)傳統(tǒng)藝術(shù)理論有著深厚的功底,在他以后的理論與實(shí)踐創(chuàng)新中,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是一個(gè)必不可少的根基,因而可以說(shuō)傅抱石的藝術(shù)根源在于中國(guó)傳統(tǒng)。
二 順應(yīng)時(shí)代潮流,應(yīng)時(shí)變法創(chuàng)新
傅抱石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最早從篆刻入手,從臨摹名家篆刻而名聲漸起。書(shū)畫(huà)方面對(duì)中國(guó)傳統(tǒng)的經(jīng)典名作都有所涉獵,主要取法于石濤的山水畫(huà)藝術(shù),主張“師古人之心,不師古人之技”。在鉆研石濤畫(huà)理的過(guò)程中,其藝術(shù)創(chuàng)作也深受石濤的影響,主張石濤倡導(dǎo)的搜盡奇峰打草稿,師法造化,對(duì)自然進(jìn)行寫(xiě)生,在繼承傳統(tǒng)的時(shí)候,真正的到自然中去面對(duì)真切的山水事物才會(huì)有所創(chuàng)造。
中國(guó)古代的點(diǎn)畫(huà)技法,從宋代米芾、米友仁父子創(chuàng)立以來(lái),經(jīng)歷元明,至清代石濤發(fā)展到了一個(gè)新的高度。傅抱石對(duì)這種技法情有獨(dú)鐘,進(jìn)行了大量的鉆研與實(shí)踐。他喜好用破舊的狼毫在宣紙上揮灑,表現(xiàn)破筆在宣紙上酣暢淋漓的效果。對(duì)自然寫(xiě)生,他根據(jù)景物的需要?jiǎng)?chuàng)立了獨(dú)特技法形式――“抱石皴”。
注重寫(xiě)生是他的藝術(shù)學(xué)習(xí)集成傳統(tǒng),走向創(chuàng)新的又一法門。傅抱石到重慶之后,更加留意自然寫(xiě)生。重慶金剛坡下的山石樹(shù)林是他異常熟悉的風(fēng)景,而蜀中大川的造化滋養(yǎng)了他的藝術(shù)。他的皴法更是根據(jù)山石地理的自然面貌進(jìn)行靈活運(yùn)用,更顯時(shí)代特色。建國(guó)后,傅抱石曾帶領(lǐng)中國(guó)代表團(tuán)到東歐訪問(wèn),寫(xiě)生大量作品。50年代末期,又行程兩萬(wàn)五千里,對(duì)中國(guó)的大自然進(jìn)行寫(xiě)生,而他對(duì)東北的天池瀑布更是情有獨(dú)鐘,曾到此處多次寫(xiě)生,作有《天池飛瀑》、《鏡泊飛泉》。
傅抱石變革的中國(guó)畫(huà),與中西合璧的中國(guó)畫(huà)存在差異。中西結(jié)合的大家,如徐悲鴻和蔣兆和是把西方的素描與中國(guó)的傳統(tǒng)國(guó)畫(huà)結(jié)合起來(lái),創(chuàng)造新的國(guó)畫(huà)面貌,這些都是中西結(jié)合的產(chǎn)物。而傅抱石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則完全不同,他吸收的是傳統(tǒng),并從傳統(tǒng)中走出來(lái),創(chuàng)造出來(lái)新的形式語(yǔ)言。他的創(chuàng)作是源于傳統(tǒng),卻并不囿于傳統(tǒng)!這讓他的創(chuàng)作表現(xiàn)出一種傳統(tǒng)繪畫(huà)的時(shí)代感。
三 傅抱石理論研究的當(dāng)代意義
中西交流讓中國(guó)的本土藝術(shù)處于非常尷尬的境地,要不要保留傳統(tǒng),要不要變法,中國(guó)藝術(shù)的精神還要不要,是我們深切關(guān)注的問(wèn)題。而傅抱石在對(duì)待民族傳統(tǒng)問(wèn)題上有獨(dú)特的見(jiàn)解。50年代末期,他先后發(fā)表講演和論文對(duì)傳統(tǒng)問(wèn)題進(jìn)行論述,如《關(guān)于中國(guó)畫(huà)的傳統(tǒng)問(wèn)題》、《筆墨當(dāng)隨時(shí)代》、《思想變了,筆墨就不能不變》等,非常鮮明地表達(dá)了自己對(duì)待傳統(tǒng)的看法――要變法,要革新,放手去創(chuàng)造!
一切非傳統(tǒng)都將成為傳統(tǒng),明代人王世貞說(shuō)“山水,大小李一變也,荊關(guān)董巨,又一變也,李成范寬,又一變也,劉李馬夏,又一變也,大癡,黃鶴,又一變也”。前時(shí)代的藝術(shù)風(fēng)格都為后人所繼承與效法,成為傳統(tǒng)。中西文化發(fā)生對(duì)撞以來(lái),中國(guó)人深感在科學(xué)文化方面與西方的差距,而紛紛向西方學(xué)習(xí),以圖中華之強(qiáng)大。改革開(kāi)放以后,文化的輸入更是日新月異,西方現(xiàn)代主義、后現(xiàn)代主義的藝術(shù)成果源源不斷地被復(fù)制到中國(guó),介紹給中國(guó)的觀眾,使人們思想發(fā)生了變革。
藝術(shù)隨時(shí)展,于是出現(xiàn)了現(xiàn)代書(shū)法、抽象水墨畫(huà)等新興藝術(shù),以圖對(duì)中國(guó)畫(huà)進(jìn)行創(chuàng)新。傅抱石在他的講演《中國(guó)繪畫(huà)之精神》中提到:中國(guó)遠(yuǎn)在唐代,王默就是用頭發(fā)作畫(huà),張 用手摸色,秦朝的烈裔用口噴顏色而成畫(huà)。藝術(shù)不是做秀,應(yīng)該更富有內(nèi)涵。由于時(shí)代的因素,人們的世界觀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大量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走向庸俗和膚淺,而現(xiàn)當(dāng)代的理論研究與藝術(shù)創(chuàng)作變成以研究這些為中心,解構(gòu)了傳統(tǒng)藝術(shù)的內(nèi)涵。傅抱石作為聯(lián)結(jié)20世紀(jì)前后期的藝術(shù)大家,對(duì)我們藝術(shù)時(shí)代的變化有更重要的研究意義和價(jià)值。他的變法立足于傳統(tǒng)走出了一條新路,對(duì)他的藝術(shù)進(jìn)行研究于我們當(dāng)下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更有啟迪!
參考文獻(xiàn):
西方藝術(shù)源起于古希臘羅馬時(shí)期,這一時(shí)期,雕塑藝術(shù)是一個(gè)主要的表現(xiàn)手段,我們可以從一些雕塑作品中一些很明顯的特點(diǎn):較少的描繪人物的面部表情和內(nèi)心世界,注重身體細(xì)節(jié)描繪,注重外部形體的刻畫(huà)。形體已經(jīng)被塑造得十分逼真,但對(duì)于面部表情的刻畫(huà)卻顯得不那么完美,雖然其“古風(fēng)式”的微笑已經(jīng)不再明顯,但仍缺乏所謂“人”的特點(diǎn)。究其原因,一方面自然是古希臘人對(duì)身體的崇尚,另一方面,也與當(dāng)時(shí)希臘的文化密不可分。在古希臘雕塑題材中,很大一部分都是以“神”為對(duì)象,而“神”理所應(yīng)當(dāng)是超越凡人的,要表現(xiàn)這種超脫,自然很難將人的喜怒哀樂(lè)施加在“神”的雕塑之上,所以,平靜、肅穆反而更能體現(xiàn)一種莊嚴(yán)的偉大。溫克爾曼就曾在其《古代藝術(shù)史》中認(rèn)為:“希臘雕塑是靜默的偉大。”但是,這種注重外在相對(duì)忽略內(nèi)在精神的觀念卻隨著時(shí)間的推移在逐漸改變。
古羅馬后期開(kāi)始,一些作品已經(jīng)開(kāi)始表現(xiàn)人物內(nèi)心的精神世界,這為當(dāng)時(shí)的藝術(shù)注入了新鮮的血液。直到文藝復(fù)興時(shí)期,一種人文精神才得以體現(xiàn),《蒙娜麗莎》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幅作品,它之所以被作為一幅名畫(huà)來(lái)看待,正是在于它對(duì)表情的刻畫(huà)在當(dāng)時(shí)是十分難能可貴的,這種對(duì)表情惟妙惟肖的刻畫(huà),使得當(dāng)時(shí)的藝術(shù)家們發(fā)現(xiàn),藝術(shù)的創(chuàng)作不僅注重外在,還要注重從外部來(lái)表現(xiàn)內(nèi)在,即由外見(jiàn)內(nèi),可以說(shuō)這是一次意義深遠(yuǎn)的變革。
文藝復(fù)興時(shí)期的藝術(shù)總的來(lái)說(shuō)繼承了古典,但同時(shí),它在繼承這一基礎(chǔ)上有了變化,可以說(shuō),這種繼承是一種回歸,但又不是完全的回歸。靜觀這幾個(gè)世紀(jì)的事物發(fā)展規(guī)律,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一個(gè)很有趣的現(xiàn)象,那就是事物的發(fā)展隨著歷史進(jìn)程的不斷前進(jìn)其發(fā)生變化的速度也逐漸加快,藝術(shù)史的發(fā)展過(guò)程也是類似。文藝復(fù)興之后,藝術(shù)流派的產(chǎn)生明顯要比之前幾個(gè)世紀(jì)都要快上許多,而不管是從浪漫主義還是到現(xiàn)實(shí)主義再到后來(lái)的現(xiàn)代派,無(wú)一不是最近幾個(gè)世紀(jì)的產(chǎn)物。
到了十八世紀(jì),藝術(shù)家們這種由注重外在轉(zhuǎn)移到表現(xiàn)內(nèi)心世界(以外在表現(xiàn)內(nèi)在)的趨勢(shì)更加明顯,但仍然還有一部分固守古典,比如安格爾,仍注重人體,并沒(méi)有通過(guò)形體注重人的內(nèi)心世界,而魯本斯和德拉克羅瓦則更加注重通過(guò)形體表現(xiàn)精神內(nèi)心。現(xiàn)實(shí)主義也同樣如此,現(xiàn)實(shí)主義與古典主義都是注重外部形象的描繪,但是現(xiàn)實(shí)主義更注重通過(guò)形象描繪形象背后的現(xiàn)象背景,再通過(guò)這些現(xiàn)象背景表現(xiàn)人的內(nèi)在精神。
我們可以看到,西方藝術(shù)發(fā)展的過(guò)程是有一定的漸進(jìn)性的,從文藝復(fù)興、古典主義,到浪漫主義時(shí)期,再到現(xiàn)實(shí)主義時(shí)期,這一系列過(guò)程都是一個(gè)不斷自我完善的否定之否定的過(guò)程,不斷的演進(jìn),不斷的改變,當(dāng)從外部形態(tài)注重情感上后,又從情感轉(zhuǎn)移到潛意識(shí)上,是一個(gè)逐步深入的過(guò)程。緊接著,20世紀(jì)便出現(xiàn)了現(xiàn)代派,即現(xiàn)代主義,現(xiàn)代主義實(shí)際上就是試圖用藝術(shù)去表現(xiàn)潛意識(shí)世界的一個(gè)產(chǎn)物,試圖表現(xiàn)我們無(wú)法控制的領(lǐng)域。總的來(lái)說(shuō),西方藝術(shù)的發(fā)展趨勢(shì)大致可總結(jié)為四個(gè)階段,那就是:外貌由外見(jiàn)內(nèi)進(jìn)入潛意識(shí)形象解體,這讓我們看到了它所代表的一種理性的、科學(xué)的、逐層深入的一種發(fā)展過(guò)程。而中國(guó)藝術(shù)的發(fā)展趨勢(shì)則是另外一條不盡相同的路徑。
二、中國(guó)藝術(shù)發(fā)展概要
中國(guó)藝術(shù)的發(fā)展趨勢(shì)從起源階段來(lái)看,還是偏重于形象的表現(xiàn),這點(diǎn)可以在先秦一些器物的裝飾圖案上看出來(lái),而這一時(shí)期的藝術(shù)從一定程度上來(lái)說(shuō)還是一種實(shí)用性的藝術(shù)。到了魏晉時(shí)期,這可以看做是中國(guó)藝術(shù)的一個(gè)大轉(zhuǎn)折、大發(fā)展的階段,它的偉大在于這一階段已經(jīng)對(duì)藝術(shù)有了一種明確的獨(dú)立的意識(shí),我們可以看到,不管是繪畫(huà)、音樂(lè)、書(shū)法藝術(shù),其藝術(shù)的自覺(jué)都是出現(xiàn)于魏晉時(shí)期的,在此之前,很少有系統(tǒng)的理論探索,也沒(méi)有將其作為獨(dú)立的系統(tǒng)來(lái)看待。“傳神論”便是在這一背景下發(fā)展起來(lái)的,“傳神”最開(kāi)始以人物為對(duì)象,認(rèn)為描繪人物不僅需要形似,更要神似,這種對(duì)內(nèi)在層面的探索是中國(guó)藝術(shù)發(fā)展的一個(gè)巨大的進(jìn)步,同時(shí),“傳神”這一思想也逐步擴(kuò)大影響,經(jīng)過(guò)不斷發(fā)展,拓展到了山水、花鳥(niǎo)畫(huà)中,變成了一個(gè)普遍的美學(xué)命題。
在加入了“神”這一元素之后,經(jīng)過(guò)幾代藝術(shù)家的不斷發(fā)展完善,一些藝術(shù)家開(kāi)始加入了自己本身的思想意識(shí)、元素,即所謂的寫(xiě)意。寫(xiě)意可以看做是所描繪對(duì)象中的“神”以及藝術(shù)家的理解、趣味的集合,即藝術(shù)家內(nèi)心當(dāng)中的意向。翻看唐宋時(shí)期的畫(huà)論就不難發(fā)現(xiàn),“寫(xiě)意”已經(jīng)被作為一種理論思想出現(xiàn)在了畫(huà)論之中。而從發(fā)展過(guò)程來(lái)看,相對(duì)于“傳神論”時(shí)期的形、神兼顧,“寫(xiě)意”由于描繪的是所謂“意境”,即由藝術(shù)家所描畫(huà)的對(duì)象的精神和藝術(shù)家本身的思想意義交融所得到的產(chǎn)物,所以藝術(shù)作品所表現(xiàn)的意義大于形象的,也就是我們所說(shuō)的意大于形,對(duì)物象的準(zhǔn)確度的描繪已經(jīng)退為次要的位置,這一趨勢(shì)直接影響了之后的藝術(shù)發(fā)展過(guò)程。
到了明清時(shí)期,“神”和“意”成為了評(píng)價(jià)藝術(shù)作品優(yōu)劣的必備元素,“神”是人的精神、內(nèi)心世界,而“意”則是藝術(shù)家本身的精神的品德。這種“神”與“意”通過(guò)不斷的演變,轉(zhuǎn)化為了一定的形式表現(xiàn)在了畫(huà)作之上,成為了強(qiáng)調(diào)筆墨趣味的大寫(xiě)意的藝術(shù)。
“筆墨趣味”是藝術(shù)發(fā)展到一定程度后的產(chǎn)物,是將精神、趣味轉(zhuǎn)換為形式的東西,它不是關(guān)注描繪的對(duì)象,而是關(guān)注用以描繪對(duì)象的筆墨本身,展現(xiàn)自己的趣味。其所體現(xiàn)的是一種生命力,是一種生命的節(jié)奏和高低起伏,也就是一種韻律化的過(guò)程。
由上面的發(fā)展過(guò)程我們可以大致看到,相對(duì)于西方藝術(shù)來(lái)說(shuō),中國(guó)藝術(shù)的發(fā)展趨勢(shì)經(jīng)歷了:外形、傳神、寫(xiě)意、韻律化四個(gè)階段,而這四個(gè)階段最終將中國(guó)的藝術(shù)大結(jié)構(gòu)導(dǎo)向了一種生命的狀態(tài),有最初的只具備形體,接著不斷注入“神”、注入“意”,進(jìn)而發(fā)展出生命所獨(dú)有的韻律的起伏,是一種讓藝術(shù)不斷具有活力,不斷具備生命特征的過(guò)程。
三、中西方藝術(shù)發(fā)展異同
那么,既然了解了中西方藝術(shù)發(fā)展的大致路徑,可以大致看到它們所存在的區(qū)別,論者認(rèn)為,從西方藝術(shù)發(fā)展史的過(guò)程來(lái)看,科學(xué)的剖析、逐步的深入是其發(fā)展的一個(gè)特點(diǎn),任何一門藝術(shù)的發(fā)展都是不能脫離同時(shí)期的社會(huì)與文化,古希臘時(shí)期,西方的科學(xué)已經(jīng)形成了構(gòu)成性的科學(xué)基礎(chǔ),即開(kāi)始探討萬(wàn)物構(gòu)成的基本元素,著名的古希臘哲學(xué)家德謨克利特就曾提出了原子是構(gòu)成事物的基本元素的這一觀點(diǎn),即原子唯物論,當(dāng)然,當(dāng)時(shí)他所提出的原子非現(xiàn)在的原子,而是一種假設(shè),即構(gòu)成事物的最基本單位,不可再分的單位。從這一點(diǎn)來(lái)看,我們我可看到,西方的科學(xué)實(shí)際上是希望將事物拆開(kāi)來(lái)看的,探究它的內(nèi)部構(gòu)成。是一種不斷深入、層層打開(kāi)的過(guò)程。這種事物構(gòu)成的觀念直接影響了藝術(shù)的發(fā)展。
【關(guān)鍵詞】 萊辛;《拉奧孔》;造型藝術(shù);美之法則
[中圖分類號(hào)]J0-02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萊辛是18世紀(jì)歐洲啟蒙運(yùn)動(dòng)的代表人物,以文藝批評(píng)、戲劇創(chuàng)作、教育理論及神學(xué)思想傳世,其中以文藝批評(píng)《拉奧孔》和《漢堡劇評(píng)》最為突出。萊辛因其文藝批評(píng)被稱為“歐洲第一位評(píng)論家”[1]33,近則歌德、席勒,遠(yuǎn)至唯美主義運(yùn)動(dòng)都深受其文藝觀點(diǎn)影響[2]325-330。萊辛生于1729年德意志卡門茨的正統(tǒng)神職人員之家,早年到萊比錫學(xué)習(xí)神學(xué),畢業(yè)后放棄擔(dān)任神職,只身前往柏林從事文字工作,在著書(shū)立說(shuō)之余也進(jìn)行戲劇創(chuàng)作。他的戲劇代表作有《薩拉·薩姆遜小姐》、《明娜·封·巴爾赫姆》及《智者納旦》等。時(shí)值啟蒙運(yùn)動(dòng)之初,萊辛大力提倡理性精神,對(duì)抗傳統(tǒng)神學(xué)并反對(duì)哲學(xué)和神學(xué)的勉強(qiáng)結(jié)盟。德意志教育在當(dāng)時(shí)基本都屬神學(xué)范疇,萊辛力主在大學(xué)和宮廷之外建立一套新的教育方案。這些觀念也反映在他的文藝主張中。
18世紀(jì)中期以前的德意志還沒(méi)有自己的文藝體系,在文藝?yán)碚撋险瞻岱▏?guó)新古典主義的套路,同時(shí)文藝復(fù)興的積淀及對(duì)古代藝術(shù)的考古新發(fā)現(xiàn)再度掀起古典藝術(shù)的熱潮,也引發(fā)古今之爭(zhēng)的大論戰(zhàn)。溫克爾曼的《古代藝術(shù)史》使古希臘藝術(shù)再次成為關(guān)注的焦點(diǎn),影響深遠(yuǎn),萊辛的《拉奧孔》主要在溫克爾曼的文藝觀點(diǎn)啟示下寫(xiě)成。《拉奧孔》在此背景下成書(shū),其文藝觀點(diǎn)既是對(duì)法國(guó)新古典主義學(xué)院派、時(shí)興的文藝趣味乃至溫克爾曼文藝觀點(diǎn)的反叛,立論之基又深深根植于它們的影響。因此《拉奧孔》中的諸多觀點(diǎn)雖頗有創(chuàng)見(jiàn),但往往包含著潛在矛盾和深刻的自反性。這些觀點(diǎn)自提出以來(lái)反響不斷,在給后來(lái)的文藝批評(píng)以啟示的同時(shí),也受到批評(píng)和質(zhì)疑。
萊辛的《拉奧孔》歷來(lái)不乏研究者,研究著述雖稱不上汗牛充棟,也可謂林林總總。由于《拉奧孔》探討的主要是詩(shī)畫(huà)之爭(zhēng)及二者區(qū)別,國(guó)內(nèi)外研究著述多將其歸入文藝?yán)碚摵臀乃嚺u(píng)范疇,切入角度各不相同,但多圍繞詩(shī)畫(huà)關(guān)系這一問(wèn)題,且對(duì)詩(shī)的規(guī)律關(guān)注較多。國(guó)外方面,這些批評(píng)散見(jiàn)于各時(shí)代的作家和學(xué)者的一般作品及綜述性的文藝批評(píng)史,如歌德曾對(duì)《拉奧孔》有過(guò)簡(jiǎn)單的評(píng)述,他同意萊辛對(duì)文藝種類界限的劃分[3]130。馬修·斯內(nèi)德在《成問(wèn)題的差異:萊辛〈拉奧孔〉中矛盾的摹仿》[4]273-289一文里提出,萊辛提出詩(shī)畫(huà)差異的立論之基是摹仿說(shuō),而摹仿本身的雙向性使論證詩(shī)畫(huà)二元對(duì)立難以成立,此外他認(rèn)為萊辛提出詩(shī)畫(huà)分野的原因在于美學(xué)受到人學(xué)威脅引起的焦慮。國(guó)內(nèi)方面情況類似,錢鐘書(shū)及朱光潛都曾著文分析評(píng)述《拉奧孔》,但專門的研究性著作至今未見(jiàn)。主要關(guān)注《拉奧孔》藝術(shù)批評(píng)觀點(diǎn)而將其歸入藝術(shù)批評(píng)史的研究?jī)A向出現(xiàn)在20世紀(jì)上半葉,在此之前未見(jiàn)將藝術(shù)批評(píng)從藝術(shù)史和美學(xué)史中獨(dú)立出來(lái)綜合考察的研究。國(guó)內(nèi)外對(duì)《拉奧孔》藝術(shù)觀點(diǎn)的探討多集中在它提出的造型藝術(shù)的法則上,其中以對(duì)美之法則的質(zhì)疑最為突出。國(guó)外方面,自從現(xiàn)代藝術(shù)出現(xiàn)并得到承認(rèn)之后,萊辛所提出的法則似乎已不攻自破,對(duì)之進(jìn)行駁斥的文章不勝枚舉,論據(jù)無(wú)一例外是難以駕馭的現(xiàn)代藝術(shù);國(guó)內(nèi)方面則往往以中國(guó)畫(huà)及畫(huà)論和萊辛提出的法則進(jìn)行比較,較有代表性的有劉石的《西方詩(shī)畫(huà)關(guān)系與萊辛的詩(shī)畫(huà)觀》[5]160,其中以中國(guó)詩(shī)畫(huà)論和西方傳統(tǒng)詩(shī)畫(huà)觀對(duì)萊辛提出的詩(shī)畫(huà)法則進(jìn)行駁斥,指出萊辛詩(shī)優(yōu)畫(huà)劣的結(jié)論建立在不客觀的比較平臺(tái)之基礎(chǔ)上。此外國(guó)內(nèi)也有對(duì)萊辛文藝觀在古今之爭(zhēng)中的立場(chǎng)和地位進(jìn)行分析的論文,如劉劍的《“古今之爭(zhēng)”中的萊辛及其〈拉奧孔〉》[6]46指出,拉奧孔的文藝觀具有回歸古典、面向現(xiàn)代的承前啟后的地位。
本文將在以往文獻(xiàn)的基礎(chǔ)上,進(jìn)一步對(duì)《拉奧孔》中的造型藝術(shù)法則進(jìn)行探討。萊辛提出的造型藝術(shù)法則有其特殊的歷史文化背景,同時(shí)作者在開(kāi)篇即已指出他的批評(píng)針對(duì)的只是經(jīng)過(guò)謹(jǐn)慎選擇的恰當(dāng)對(duì)象(1)(P2),這就決定了這些法則并非放之四海而皆準(zhǔn),且或多或少帶有一定的潛在矛盾。本文從造型藝術(shù)法則的具體內(nèi)容入手,闡明“美”在萊辛的實(shí)際論證中并不是造型藝術(shù)的最高法則,而萊辛提出的美的標(biāo)準(zhǔn)也包含了諸多自反性與分裂性,從歷史上看,它們預(yù)示著現(xiàn)代藝術(shù)及其法則的誕生。在萊辛提出的法則業(yè)已遭到取締的今天,現(xiàn)代藝術(shù)及其法則的混亂現(xiàn)狀又促使人們重新回到萊辛法則的合理性中尋找出路。
一、造型藝術(shù)的最高法則不是“美”
萊辛的《拉奧孔》以“為什么拉奧孔在雕刻里不哀號(hào),而在詩(shī)里卻哀號(hào)?”這一問(wèn)題開(kāi)篇,提出和溫克爾曼不同的見(jiàn)解,并論證了希臘造型藝術(shù)的理想不是溫克爾曼所說(shuō)的“偉大的靜穆和高貴的單純”,而是“美”。通觀《拉奧孔》全篇,萊辛推崇的是希臘人的藝術(shù),在對(duì)造型藝術(shù)的要求上,他也以希臘為理想范本,認(rèn)為“明智的希臘人”使造型藝術(shù)只摹仿美的物體(P8)。另一方面,從造型藝術(shù)本身的規(guī)律來(lái)看,他指出造型藝術(shù)是空間藝術(shù),描繪空間中并列的物體[7]293,“美”存在于空間中的物體,物體美要求空間中各部分的并列及和諧,因此造型藝術(shù)最宜于表現(xiàn)美,也最易于通過(guò)表現(xiàn)美獲得成功。他由此提出美是造型藝術(shù)的最高法則,理想的造型藝術(shù)“如果和美不相容,就須給美讓路;如果和美相容,也至少須服從美”(P11)。將美作為最高法則的論點(diǎn)由此建立,然而從這一論點(diǎn)提出的目的、依據(jù)及論證過(guò)程看,它是深可質(zhì)疑的。
首先萊辛之所以提出和強(qiáng)調(diào)美的法則,是為了通過(guò)提出理想的造型藝術(shù)范式反對(duì)那些他認(rèn)為不得體的造型藝術(shù),這些造型藝術(shù)之所以得不到他的認(rèn)可,是因?yàn)樗鼈兓煜嗽?shī)畫(huà)的界限,在造型藝術(shù)中追求它不該追求的東西。因此提出這一法則更深層的目的是指明詩(shī)和畫(huà)的不同。《拉奧孔》書(shū)名的副標(biāo)題就叫“論詩(shī)與畫(huà)的界限”,書(shū)中各種論證及法則基本都是為“界定”這一目的服務(wù),提出造型藝術(shù)存在于空間也是為了與詩(shī)的“時(shí)間”存在方式相區(qū)別。其次,書(shū)中提出的諸多法則在論證的過(guò)程中主要通過(guò)詩(shī)畫(huà)爭(zhēng)勝的結(jié)果得以成立。其中有兩個(gè)問(wèn)題值得注意。其一,《拉奧孔》論證了在對(duì)物體美的表現(xiàn)上,詩(shī)不如畫(huà),而畫(huà)只應(yīng)該追求美,然而作者卻用了三章的篇幅來(lái)考證拉奧孔的詩(shī)和畫(huà)之間是否存在摹仿或抄襲的關(guān)系,提出了“獨(dú)創(chuàng)性”這個(gè)評(píng)判標(biāo)準(zhǔn)。指出假如并非獨(dú)創(chuàng),那么無(wú)論是畫(huà)還是詩(shī)在價(jià)值上都要大打折扣。可見(jiàn)在美這一純感官體驗(yàn)之外,造型藝術(shù)還存在著另一個(gè)重要的評(píng)判標(biāo)準(zhǔn)。假如沒(méi)有獨(dú)創(chuàng)性,即便造型藝術(shù)本身是美的也要貶值。作者此處預(yù)設(shè),只有美還不足以使造型藝術(shù)贏得聲名,筆者推斷,這主要是因?yàn)閱渭兊脑煨退囆g(shù)之美所引起的感官愉悅不足以“讓人長(zhǎng)期地反復(fù)玩索”(P16),也就是說(shuō),獨(dú)創(chuàng)性和造型藝術(shù)的“時(shí)間性”密切相關(guān)。
其二,延續(xù)由“獨(dú)創(chuàng)性”引出的“時(shí)間性”這一推斷,筆者發(fā)現(xiàn)“時(shí)間性”匪夷所思地成為了造型藝術(shù)的評(píng)判標(biāo)準(zhǔn),而造型藝術(shù)誠(chéng)如萊辛論證過(guò)的,是空間藝術(shù)。萊辛指出,造型藝術(shù)之美在于其所摹仿的美的物體,而物體的美在于空間中物體的并列與和諧,也即比例合當(dāng),符合數(shù)學(xué)規(guī)律。然而萊辛在解釋為什么造型藝術(shù)不宜表現(xiàn)激情頂點(diǎn)的頃刻時(shí),他認(rèn)為指出美的法則還嫌單薄,于是提出造型藝術(shù)局限于頃刻,為了讓其更為“耐看”,必須選擇包孕最豐富時(shí)間的一刻,也即激情頂點(diǎn)前的一刻。說(shuō)明作者認(rèn)為,空間藝術(shù)在時(shí)間性上的品質(zhì)比美的法則更具說(shuō)服力。回到美之法則提出的原因上,“美”不僅服務(wù)于區(qū)分詩(shī)畫(huà)的任務(wù),而且并不是評(píng)判造型藝術(shù)的全部?jī)r(jià)值,作者提出的其他評(píng)判標(biāo)準(zhǔn)無(wú)一例外建立在“如何實(shí)現(xiàn)造型藝術(shù)存在的最大可能性”這一基本問(wèn)題上。包括美的準(zhǔn)則在內(nèi),《拉奧孔》中提出的造型法則始終圍繞詩(shī)畫(huà)爭(zhēng)勝這一基本前提,它們的價(jià)值僅體現(xiàn)在勘定造型藝術(shù)的領(lǐng)地上,其目的是使造型藝術(shù)盡可能地?zé)o可取代并占有盡可能多的維度(時(shí)間和空間)。
誠(chéng)如文杜里指出,美的法則早已有之,萊辛的功績(jī)?cè)谟趧?chuàng)造了“造型藝術(shù)”這一對(duì)繪畫(huà)、雕塑和建筑使用的統(tǒng)稱,在此之前它們被稱為“美的藝術(shù)”(P101)。萊辛根據(jù)他的發(fā)現(xiàn)提出這一名稱,而他的發(fā)現(xiàn)正是這一藝術(shù)門類的共同法則并非“美”,而是“造型”本身。這一發(fā)現(xiàn)擴(kuò)充了此門類的法則,但問(wèn)題來(lái)了,“造型”就如同“美”一樣,宣稱其法則和分類依據(jù)就是其意義難免有同義反復(fù)之嫌。假如提出在實(shí)現(xiàn)造型藝術(shù)最大可能性的過(guò)程中仍然少不了美的標(biāo)準(zhǔn),那么在美的標(biāo)準(zhǔn)中也存在著諸多分裂性。
二、美的標(biāo)準(zhǔn)中包含的分裂性與自反性
假如我們能夠接受現(xiàn)代藝術(shù),從接納了現(xiàn)代藝術(shù)的藝術(shù)史的角度來(lái)看《拉奧孔》中的“美”,就會(huì)發(fā)現(xiàn)萊辛所說(shuō)的“美”指的是審美之美,而非藝術(shù)之美。二者的區(qū)別在于前者指的是符合比例的自然物造成的純粹感官的愉悅,它的前提是摹仿說(shuō),即認(rèn)為造型藝術(shù)之美在于摹仿美的物體;后者注重藝術(shù)本身的形式與意義,即便是丑的事物也能以藝術(shù)的形式或其背后的意義給觀眾造成愉悅之感。現(xiàn)代藝術(shù)的合法性建立在后者的基礎(chǔ)上。包括歌德、文杜里在內(nèi)的許多人指責(zé)萊辛將批評(píng)原則降低到自然物理性的水平[3]102,并非沒(méi)有道理。自然物理性跟“美”掛鉤,得益于心理科學(xué),也必須依賴變幻不定的心理體驗(yàn)。心理機(jī)制可以通過(guò)教育進(jìn)行塑造和改造,萊辛就終身致力于塑造德意志的民族心理。通過(guò)心理改造,美感也會(huì)隨之發(fā)生改變。“模糊的,有時(shí)甚至是武斷的心靈狀態(tài),就用相對(duì)性的藝術(shù)趣味代替了藝術(shù)的法則。”[3]88萊辛所推崇的法則在深層邏輯上指向現(xiàn)代藝術(shù)的變異,與唯美主義及現(xiàn)代藝術(shù)的主張并不矛盾。羅杰·弗萊就提出由變革藝術(shù)教育可以促成藝術(shù)趣味的改變這一觀點(diǎn),在他看來(lái)造型藝術(shù)的“審美”已不是問(wèn)題所在,“風(fēng)格”取代之成為關(guān)鍵詞,只要風(fēng)格得到承認(rèn),作品之間就不存在絕對(duì)差距,而只有風(fēng)格上的相對(duì)差異,一切都可以被解釋為美的[8]132。包括《拉奧孔》中認(rèn)為低于美的丑、可笑、可怖和崇高。
萊辛在文藝觀上反對(duì)法國(guó)新古典主義的趣味(P6),提出“美”這一準(zhǔn)則為的是區(qū)別于與他同時(shí)代的美術(shù)趣味追求的不合宜事物,然而“美”正是典型的新古典主義理想。[9]37和新古典主義的取向一樣,萊辛反對(duì)造型藝術(shù)追求“妙肖原物”,認(rèn)為希臘之所以少見(jiàn)寫(xiě)真的雕像,是因?yàn)榉梢笤煨退囆g(shù)遵循美的精神,減少“平庸的逼真像”(P10)。即是說(shuō)萊辛既認(rèn)可藝術(shù)描摹自然,又反對(duì)它描寫(xiě)自然之“真”,而要求它以理想的自然為描繪對(duì)象。這不僅與新古典主義的主張不謀而合,還昭示著其又一分裂性。萊辛提出“美”直接反對(duì)的是“真”和外在于作品內(nèi)容的藝術(shù)技巧本身,他認(rèn)為這兩者只能產(chǎn)生“空洞而冷淡的”,這是追求理想藝術(shù)的藝術(shù)家所不以為然的(P6)。但同時(shí),萊辛所提倡的物體美,并不屬于確然實(shí)在的物體本身,而屬于理想的物體,即合乎數(shù)學(xué)法則的物體比例。因此歸根到底,這同樣是外在于作品內(nèi)容的理性法則,屬于他自己反對(duì)的藝術(shù)技巧。他所推崇的美之法則最終總是起而法則自身,足見(jiàn)這一法則潛在的自反性。
在古今之爭(zhēng)的論戰(zhàn)中,萊辛無(wú)疑站在古代藝術(shù)的陣營(yíng),《拉奧孔》中引以為據(jù)的正面案例基本都是古代藝術(shù)。啟蒙時(shí)代和浪漫時(shí)代在藝術(shù)趣味方面都有一個(gè)共同的特征,即摒棄自己的時(shí)代,在古代藝術(shù)中尋找理想。盡管古今之爭(zhēng)中兩大陣營(yíng)實(shí)力對(duì)比懸殊,當(dāng)代藝術(shù)支持者的地位及話語(yǔ)的分量遠(yuǎn)不及它的對(duì)手,然而二者的依據(jù)都屬于新古典主義。古典主義者所崇尚的古代的美之理想不但沒(méi)有被對(duì)手,反而是對(duì)手提倡的美學(xué)主張的依據(jù)。支持當(dāng)代藝術(shù)的進(jìn)步主義者假定美的理想亙古不變,知識(shí)、文明及理性的進(jìn)步帶來(lái)的藝術(shù)技巧及法則的進(jìn)步只會(huì)讓現(xiàn)代人更容易接近美的理想(P38)。作為古代藝術(shù)倡導(dǎo)者的萊辛也持這種觀點(diǎn),認(rèn)為如今的造型藝術(shù)在技法上比古代有了進(jìn)步(P111)。在美的理想不變的基礎(chǔ)上,萊辛的這種信念必定可以推衍出今勝于古的結(jié)論,從而使其立場(chǎng)導(dǎo)向現(xiàn)代。假如現(xiàn)代性就是一種“反對(duì)自身的傳統(tǒng)”[9]102,那么可以說(shuō),萊辛所提出的美的法則同樣具有這種特征,它的分裂性和自反性預(yù)示著現(xiàn)代藝術(shù)的來(lái)臨。
三、現(xiàn)代藝術(shù)的混亂及美之法則的合理性
在18世紀(jì)這一“美學(xué)的偉大時(shí)代”,“美是唯一被藝術(shù)家和思想家積極思考的美學(xué)品質(zhì)”。[10]7離開(kāi)被美的觀念主宰的18世紀(jì),進(jìn)入現(xiàn)代藝術(shù)的領(lǐng)域,現(xiàn)代藝術(shù)詮釋了黑格爾關(guān)于藝術(shù)美為何好像高于自然美的注解:藝術(shù)美是“由心靈產(chǎn)生的美和再生的美”,即藝術(shù)美已經(jīng)跳脫摹仿論的桎梏,不再是自然產(chǎn)品,而“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知性產(chǎn)品”[10]12。也就是說(shuō),真和善,甚至是“新”這些有關(guān)知性的品質(zhì)成為比美更為重要的評(píng)判標(biāo)準(zhǔn),因?yàn)槿缃袼囆g(shù)品與人類心靈的關(guān)系導(dǎo)向?qū)χ杂欣囊幻妫@是現(xiàn)代性之建立的結(jié)果,也是其重要的表現(xiàn)之一。知性的獲勝帶來(lái)的是美的廢黜。因?yàn)椤懊馈保辽偈沁^(guò)去藝術(shù)批評(píng)中的審美之美已經(jīng)無(wú)能解釋獲得合法地位的現(xiàn)代藝術(shù)。同時(shí)為了追求知性,就不得不摒棄“美”這種帶有粉飾意味的特質(zhì),因?yàn)榉埏椀暮圹E是對(duì)知性的損害。在這一意義上,“美本身讓擁有它的東西變得無(wú)足輕重”[10]11。由是我們看到,萊辛認(rèn)為造型藝術(shù)不宜表現(xiàn)的東西都在現(xiàn)代藝術(shù)中得到了表現(xiàn)。
但另一方面,現(xiàn)代藝術(shù)及其法則的混亂現(xiàn)狀又往往使人質(zhì)疑它的合法性。仍以造型藝術(shù)為例:它是否能夠像它承諾的那樣揭示真和善?這頗為可疑。首先無(wú)論造型藝術(shù)的形式如何千變?nèi)f化,它終歸是視覺(jué)藝術(shù)。胡塞爾在他的圖像意識(shí)現(xiàn)象學(xué)中提出,我們?cè)谥庇^現(xiàn)象時(shí),就已經(jīng)不可避免地帶有“形而上”的“本質(zhì)的看”。“本質(zhì)的看”和“表象的看”并置在我們對(duì)圖像的直觀之中,本質(zhì)沒(méi)有決定表象,相反,以圖像事物為基礎(chǔ)的表象卻能夠左右我們對(duì)本質(zhì)的想象和認(rèn)識(shí)。[11]2對(duì)視覺(jué)來(lái)說(shuō),在觀看圖像的時(shí)候,表象和本質(zhì)無(wú)法分開(kāi),圖像本身無(wú)法決定我們將看到什么,圖像如何進(jìn)入意識(shí),依靠的仍然是既定的機(jī)制,得知的信息和引起的思考仍然是事先或事后另行附加于我們的觀念。如此一來(lái)它就無(wú)法告訴我們不知道的事情,而它所證明的是我們已有的觀念。因此,造型藝術(shù)看來(lái)與知性是無(wú)緣的。
除卻真和善,假若“新”也是一條法則,那么它所導(dǎo)向的也終歸是藝術(shù)品光芒的稍縱即逝和虛無(wú)主義。因?yàn)橐浴靶隆睘樵u(píng)判標(biāo)準(zhǔn)必然使藝術(shù)品不再“試圖加入現(xiàn)時(shí),而是要在時(shí)間上超越自身,以求置身于未來(lái)”,讓它們不僅與過(guò)去決裂,也徹底破除現(xiàn)時(shí)。[12]42藝術(shù)品的身份與價(jià)值決定于構(gòu)成藝術(shù)史的過(guò)去,未來(lái)只有與身份相聯(lián)系才與藝術(shù)品主體有關(guān),因此未來(lái)產(chǎn)生于過(guò)去,拋棄過(guò)去、割裂當(dāng)下也就沒(méi)有可以稱得上“未來(lái)”的東西。造型藝術(shù)以“新”為法則必然導(dǎo)向其自身的頹廢和衰亡。
究其根本,包括造型藝術(shù)在內(nèi),藝術(shù)的法則仰賴于飄忽不定的心理科學(xué),因此藝術(shù)的身份證及桂冠的授予最終依托的還是使其合法的闡釋。這種闡釋是否能夠使藝術(shù)品引起人們的心靈反應(yīng)決定了藝術(shù)品的價(jià)值。而要分辨這種心靈反應(yīng)是由藝術(shù)品的真、善、美還是其他品質(zhì)引起的,要辨析不同的品質(zhì)引發(fā)的心靈反應(yīng)之不同究竟在哪里,則幾乎是不可能的。誠(chéng)如萊辛在《拉奧孔》開(kāi)篇闡明的那樣,他所做的藝術(shù)批評(píng)只是“片面”的闡釋,并且只是依托于心理學(xué)的闡釋而已(P2),并沒(méi)有挖掘普遍真理或制定普遍藝術(shù)法則的意圖。現(xiàn)代藝術(shù)及其法則的混亂主要是各種意見(jiàn)妄圖一統(tǒng)天下的結(jié)果,而各種意見(jiàn)的根本依據(jù)依然是不完善的心理科學(xué)。美之法則雖有諸多缺陷,但僅僅作為一種意見(jiàn)未必沒(méi)有合理之處。至少它要求造型藝術(shù)追求的是造型藝術(shù)可以追求的東西,而非越界的“知性”或虛妄的“新”。歸根到底,藝術(shù)的界限和價(jià)值并不由藝術(shù)法則決定,而靠現(xiàn)實(shí)的藝術(shù)作品來(lái)劃定和豐富,啟示研究藝術(shù)的人如此這般的作品也能引起人們的心靈反應(yīng)。因此,美之法則不僅不應(yīng)輕易排除,在藝術(shù)面臨各種危機(jī)的當(dāng)今,其合理性更應(yīng)引起人們的注意和反思。
四、結(jié)語(yǔ)
現(xiàn)代藝術(shù)的出現(xiàn)及合法化使萊辛的《拉奧孔》針對(duì)造型藝術(shù)提出的美之法則,乃至整個(gè)啟蒙時(shí)代及新古典主義美學(xué)的理想都遭到懷疑。萊辛在《拉奧孔》中提出美的理想是為了界定造型藝術(shù)的領(lǐng)域,為了強(qiáng)調(diào)詩(shī)與畫(huà)的差異,而論證的過(guò)程是把詩(shī)畫(huà)進(jìn)行比較,讓二者爭(zhēng)勝。造型藝術(shù)的最高法則的提出從目的、論證及論據(jù)來(lái)看都是造型藝術(shù)本身,因此出現(xiàn)了在一些場(chǎng)合美之法則讓位于其他法則的矛盾情況。美作為造型藝術(shù)的最高法則這種提法包含著諸多內(nèi)在矛盾,不僅如此,作為一種批評(píng)標(biāo)準(zhǔn)的美也內(nèi)含分裂性與自反性,這和《拉奧孔》成書(shū)的特殊背景及作者本身的取向密切相關(guān)。縱觀近現(xiàn)代藝術(shù)史,這些分裂性與自反性最終導(dǎo)向的是現(xiàn)代藝術(shù)及其法則。現(xiàn)代藝術(shù)趣味的轉(zhuǎn)向要求取締美之法則的合法性,然而現(xiàn)代藝術(shù)本身的自相矛盾和混亂比它所反對(duì)的東西可疑得多。在一一質(zhì)疑現(xiàn)代藝術(shù)之理想的同時(shí),回顧美之法則的合理性在所難免。當(dāng)今藝術(shù)之危機(jī)更要求人們回到萊辛,回到藝術(shù)之歷史中求索原因和解救之法。正如同在自反性之中進(jìn)行創(chuàng)造的現(xiàn)代性一樣,《拉奧孔》中造型藝術(shù)最大的價(jià)值興許同樣在于在有局限的空間創(chuàng)作中追求不可能的時(shí)間性。
參考文獻(xiàn):
[1]威廉·狄爾泰. 體驗(yàn)與詩(shī)[M].胡其鼎,譯. 北京:生活·讀書(shū)·新知三聯(lián)書(shū)店,2003.
[2]Lessing[J]. The Crayon. 1856, 3(11).
[3]里奧奈羅·文杜里. 西方藝術(shù)批評(píng)史[M].遲軻,譯. 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
[4]Schneider, Matthew. Problematic Differences: Conflictive Mimesis in Lessing’s “Laocoon” [J]. Poetics Today. 1999, 20(2).
[5]劉石. 西方詩(shī)畫(huà)關(guān)系與萊辛的詩(shī)畫(huà)觀[J].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2008(6).
[6]劉劍.“古今之爭(zhēng)”中的萊辛及其《拉奧孔》[J].集美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09(10).
[7]張中載,趙國(guó)新.西方古典文論選讀[G].北京:外語(yǔ)教學(xué)與研究出版社,2000.
[8]羅杰·弗萊. 弗萊藝術(shù)批評(píng)文選[M].沈語(yǔ)冰譯.南京:江蘇美術(shù)出版社,2010.
[9]馬泰·卡林內(nèi)斯庫(kù). 現(xiàn)代性的五副面孔——現(xiàn)代主義、先鋒派、頹廢、媚俗藝術(shù)、后現(xiàn)代主義[M].顧愛(ài)彬,李瑞華,譯. 北京:商務(wù)印書(shū)館,2009.
[10]阿瑟·C.丹托.美的濫用:美學(xué)與藝術(shù)的概念[M].王春辰,譯.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
關(guān)鍵詞:戰(zhàn)爭(zhēng)敘事;空間;境;虛;實(shí)
中圖分類號(hào):J802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時(shí)間和空間總是一對(duì)相互聯(lián)系起來(lái)的概念,任何事物都會(huì)占據(jù)一定的空間,或者呈現(xiàn)一定的空間,但同時(shí),也占用了一段時(shí)間,或者一個(gè)瞬間,否則,事物無(wú)法存在,而且人們也無(wú)法認(rèn)識(shí),更不能談理解了。藝術(shù)作品是一種時(shí)間和空間的二維結(jié)合,它只有具備了這兩個(gè)因素之后,才能談到解讀與認(rèn)識(shí)。因?yàn)椋耙粋€(gè)事件是發(fā)生于特定時(shí)刻和空間定的一點(diǎn)的某種東西”。①
敘事空間往往側(cè)重于敘事橫向發(fā)展的一面。一般認(rèn)為,它包括故事空間和話語(yǔ)空間。故事空間往往指敘述的事件發(fā)生的場(chǎng)所,而話語(yǔ)空間則指的是敘述行為發(fā)生的場(chǎng)所或者環(huán)境。就以雷馬克的《西線無(wú)戰(zhàn)事》為例,小說(shuō)采取的是第一人稱復(fù)數(shù)“我們”來(lái)敘述,同名電影的鏡頭也是隨著主人公保羅跟進(jìn),主要也是表現(xiàn)“我們”,基本上是一致的。“我們”的敘述行為隨著故事的發(fā)展,場(chǎng)所在變換,先是學(xué)校、戰(zhàn)場(chǎng)(主要是戰(zhàn)壕)、家,而敘述行為基本上發(fā)生在戰(zhàn)場(chǎng),于是戰(zhàn)場(chǎng)就成為了敘述行為的話語(yǔ)空間,而學(xué)校、家、戰(zhàn)壕這些不同的地點(diǎn)則構(gòu)成了敘事行為的故事空間。故事空間實(shí)際上是敘事發(fā)生的背景,或者場(chǎng)景,給故事的展開(kāi)提供一個(gè)可信的環(huán)境,以達(dá)到似真的效果。即“從最基本的層面講,小說(shuō)對(duì)于背景的描述使得讀者能夠?qū)θ宋锛捌湫袆?dòng)進(jìn)行視覺(jué)化處理,由此增強(qiáng)故事的可信度,同時(shí)使得人物更加生動(dòng)、真實(shí)”。②
小說(shuō)等以文字為手段的敘事作品,在敘事過(guò)程中,存在著將其“視覺(jué)化”的過(guò)程,而故事的發(fā)展往往總會(huì)使得讀者在理解、接受的過(guò)程中,存在著將其無(wú)意識(shí)地“視覺(jué)化”,即讀者可能會(huì)在腦海中借助于想象形成一幅幅畫(huà)面的感知空間。這些呈動(dòng)態(tài)特征的畫(huà)面不再是簡(jiǎn)單的故事空間和話語(yǔ)空間的關(guān)系,更類似于電影的時(shí)空組合。重新構(gòu)建的畫(huà)面已經(jīng)脫離了原有的背景或者場(chǎng)景,進(jìn)入到一個(gè)意象氛圍的空間,成為一個(gè)具有獨(dú)立特性的敘事單元。空間不再是故事發(fā)生的地點(diǎn)和敘事必不可少的場(chǎng)景,而是利用空間來(lái)呈現(xiàn)時(shí)間,利用空間來(lái)安排整個(gè)作品的敘事結(jié)構(gòu),甚至利用空間來(lái)推動(dòng)整個(gè)敘事進(jìn)程。
W. J.T.米歇爾在其論文《文學(xué)中的空間形式:走向一種總體理論》一文探討了敘事作品的空間形式問(wèn)題。在這篇文章中,米歇爾提出了文學(xué)空間形式的四種類型:字面層,提供了文本的物理存在形式,它只是一個(gè)物的存在;描述層,即作品中表現(xiàn)、描述出來(lái)的世界;文本表現(xiàn)的事件序列,它呈現(xiàn)為一種時(shí)間形式;故事背后的意蘊(yùn),它是一種形而上的空間形式。空間敘事的形式就是從字面層意義、作品描述的意思以及所呈現(xiàn)的時(shí)間序列而進(jìn)入敘事空間的形式,即產(chǎn)生的一個(gè)新的敘事形式,這一形式包容著形而下的所有層面,也涵蓋了形而上的意義,是一個(gè)充滿了情感、認(rèn)知與理解的意蘊(yùn)空間,更是一種“境”。正如米克·巴爾所說(shuō),“當(dāng)幾個(gè)地點(diǎn)按組排列起來(lái)時(shí),就可與精神的、意識(shí)形態(tài)的和道德的對(duì)立相關(guān)聯(lián),場(chǎng)所可以作為一個(gè)重要的結(jié)構(gòu)原則起作用”。③雖然米克·巴爾還只是停留在經(jīng)典敘事學(xué)的范疇來(lái)看空間形式的,卻也暗示著空間發(fā)展的可能。
一 空間敘事的典型表現(xiàn)形式:戰(zhàn)爭(zhēng)敘事
人既是時(shí)間存在,也是空間存在。只不過(guò)在生活中,人們只重視了自己明顯感覺(jué)到意識(shí)到的時(shí)間,而并沒(méi)有開(kāi)發(fā)自己的空間意識(shí)罷了。人們空間位置的位移、變動(dòng)其實(shí)同時(shí)間一樣,也在不停地變化著,只是不像對(duì)于時(shí)間那樣敏感而已。而目前人們對(duì)于空間的重視,正如舒爾茲所說(shuō),“人之對(duì)空間感興趣,其根源在于存在。它是由于人抓住了在環(huán)境中生活的關(guān)系,要為充滿事件和行為的世界提出意義或秩序的要求而產(chǎn)生的”。④人要為自己的存在進(jìn)行定位,做出解釋,或者賦予某種形而上的意義。從而,藝術(shù)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就成為這一內(nèi)在要求的反映。而在詹姆遜看來(lái),在后現(xiàn)代社會(huì),時(shí)間已經(jīng)被極端地壓縮了,甚至人們對(duì)時(shí)間的經(jīng)驗(yàn)正在替換為空間的經(jīng)驗(yàn),是時(shí)間性終結(jié)的時(shí)代。柏格森所依賴的綿延時(shí)間以及普魯斯特等現(xiàn)代主義者迷戀的深度空間已經(jīng)蕩然無(wú)存,一切都將終止于身體和此刻。如詹姆遜就認(rèn)為,功夫電影已經(jīng)不再有情節(jié)了,這一類型的電影每分鐘都充斥著爆炸性事件。這一點(diǎn),也體現(xiàn)在藝術(shù)作品的戰(zhàn)爭(zhēng)敘事之中。
就藝術(shù)作品的敘事空間而言,它是作者對(duì)故事或事件中原本就有的空間表現(xiàn)進(jìn)行取舍、處理以及重組的結(jié)果,是作者認(rèn)為的最具代表性和最適合故事或事件中的事物活動(dòng)或存在的空間,是一個(gè)由作者運(yùn)用多種不同的表現(xiàn)手段建構(gòu)而成的一個(gè)由文字、色彩、影像以及聲音構(gòu)成的意象性空間。戰(zhàn)爭(zhēng)敘事的敘事空間也僅僅只是其中的一個(gè)類型。在這一空間中,作者借助敘事,構(gòu)建了一個(gè)有關(guān)戰(zhàn)爭(zhēng)的故事、事件及其理解和意識(shí),而讀者或者觀眾則借助于這一意象空間,盡可能重構(gòu)那個(gè)由作者傳達(dá)的故事,理念,進(jìn)而進(jìn)入審美的空間,這一敘事空間是二者進(jìn)行理性認(rèn)識(shí)以及審美交流的平臺(tái)。始終貫穿了從社會(huì)生活到故事空間,再?gòu)墓适驴臻g到敘事空間,從敘事空間到審美空間這樣一個(gè)特征的交流過(guò)程。盡管在這一敘事過(guò)程中,存在著差異,比如文字與圖像媒介本身之間的不同,可能導(dǎo)致的效果之間的差異。如戰(zhàn)爭(zhēng)小說(shuō)與戰(zhàn)爭(zhēng)電影、繪畫(huà)、雕刻等之間的不同,具體到作品,如約瑟夫·海勒的同名小說(shuō)與電影《第二十二條軍規(guī)》之間的差異。
但由于“空間永遠(yuǎn)不是一種單純的框框,也不是一種真實(shí)的描述性環(huán)境,而是一種特殊的‘戲劇容積’”,⑤故事中人物的生存與活動(dòng)空間的融合,它必然承載著某一地域、時(shí)代、歷史、民族、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階級(jí)、地位等各方面人文領(lǐng)域的內(nèi)涵,也包含著其思想、情感、心理、心靈、道德等方面的重要內(nèi)容。因而,“我們應(yīng)該尋找一種確切的方式去理解敘事作品表現(xiàn)的空間性以及作品描述的空間與其它結(jié)構(gòu)成分之間的關(guān)系”。⑥相對(duì)于戰(zhàn)爭(zhēng)敘事而言,其敘事空間是在敘事時(shí)間呈現(xiàn)點(diǎn)敘事的特征下表現(xiàn)出來(lái)的一種動(dòng)態(tài)的意象空間,是一個(gè)個(gè)時(shí)間點(diǎn)之下所呈現(xiàn)的空間。因此,敘事空間是在線性敘事的鏈條中營(yíng)造空間,通過(guò)一個(gè)富有意義的意象,通過(guò)有效的、強(qiáng)有力的敘事空間的表現(xiàn),來(lái)把故事講得富于感染力。不僅如此,這一敘事空間必然展現(xiàn)了某一地域、民族、時(shí)代等信息,也展現(xiàn)著在上面的大背景之下人們的意識(shí)、情感等內(nèi)容。這樣,就使得敘事中的空間從故事發(fā)生的地點(diǎn)、場(chǎng)景、空間走向空間意象之外,從而超越了僅僅局限于人物活動(dòng)場(chǎng)所的空間意義,從作品的敘事空間走向空間敘事,使得空間具有了在時(shí)空關(guān)系的背景上的獨(dú)立的意義。即從敘事空間走向空間敘事,使得空間在戰(zhàn)爭(zhēng)敘事中具有一份獨(dú)特的魅力。
從受眾的角度來(lái)看,敘事作品中地點(diǎn)、背景、行動(dòng)發(fā)生的場(chǎng)景等不只是提供了一個(gè)基本的時(shí)空條件,在觀看、閱讀的過(guò)程中,受眾在無(wú)意識(shí)注重的是時(shí)空關(guān)系基礎(chǔ)上呈現(xiàn)出來(lái)的景觀、文字傳達(dá)的意義或者經(jīng)過(guò)文字想象而來(lái)的景象。這里空間已經(jīng)從背景、場(chǎng)景中脫離出來(lái),具有獨(dú)立的敘事功能,是一種空間形式。
從敘事空間走向空間敘事,應(yīng)該來(lái)說(shuō),也是優(yōu)秀的敘事作品具有的特色,但對(duì)于戰(zhàn)爭(zhēng)敘事而言,其敘事的極端性將會(huì)進(jìn)一步使得敘事空間更加脫離最初的空間僅僅提供了故事發(fā)生的背景、環(huán)境、場(chǎng)景的意義,而走向獨(dú)立的外空間,以震撼或者驚異、驚奇的特征,凸顯戰(zhàn)爭(zhēng)及人的本質(zhì)特性,即詹姆遜所提到的“奇異性”。也就是說(shuō),戰(zhàn)爭(zhēng)敘事的時(shí)空關(guān)系是一種極端環(huán)境,極端場(chǎng)景,或者極端的時(shí)空背景,這一極端性的敘事場(chǎng)景將人們置于完全不同于日常生活經(jīng)驗(yàn)的空間環(huán)境之中,時(shí)刻接受著生存與死亡,愛(ài)與恨的極端體驗(yàn),一種兩難抉擇的困境,而不是日常生活中的選擇。其代價(jià)往往是沉重的,甚至以個(gè)體的生命為代價(jià)。而日常生活或者其它題材的敘事,往往達(dá)不到這一極端的程度和深度,在這一方面,戰(zhàn)爭(zhēng)敘事的極端性表現(xiàn)出來(lái)的特征非其它題材所能比。
另外,戰(zhàn)爭(zhēng)本身就是一個(gè)動(dòng)作性極強(qiáng)的詞語(yǔ),在人們的意識(shí)以及想象之中,戰(zhàn)爭(zhēng)必然存在著暴力,而暴力必然連接著一系列的動(dòng)作、場(chǎng)面,人們只是用一個(gè)簡(jiǎn)單的名詞將其豐富的內(nèi)涵掩蓋了起來(lái),正如拉康所講到的,這一現(xiàn)象,他稱之為“黑格爾的謀殺的形象”。他說(shuō)科耶夫曾經(jīng)舉過(guò)一個(gè)生動(dòng)的例子,當(dāng)我們用“狗”這個(gè)概念來(lái)指認(rèn)現(xiàn)實(shí)中的狗時(shí),“這個(gè)詞已經(jīng)不會(huì)跑、不能喝水、也不能吃東西:詞語(yǔ)中的意義(本質(zhì))不再是活的——即它已經(jīng)死了”。⑦從抽象概念走向現(xiàn)實(shí)的具體世界的過(guò)程,就是一個(gè)在無(wú)意識(shí)中殺死感性存在物的過(guò)程。同樣地,戰(zhàn)爭(zhēng)所能夠體現(xiàn)的一切內(nèi)涵包括那些動(dòng)態(tài)的過(guò)程,在概念之中遭到掩蓋了。從這一方面講,藝術(shù)世界中的戰(zhàn)爭(zhēng)敘事實(shí)際上是某種程度上的人的意識(shí)的還原過(guò)程,將過(guò)去發(fā)生的或者現(xiàn)在正在進(jìn)行的戰(zhàn)爭(zhēng)進(jìn)行還原,而這一還原或者記錄的過(guò)程,就是一個(gè)將空間中的事情敘述出來(lái)的過(guò)程,其本身所具有的激烈的沖突就內(nèi)在地含有極強(qiáng)的空間性,或者說(shuō),戰(zhàn)爭(zhēng)敘事本身已經(jīng)具備了很好的空間形式。而這一空間形式,在日常生活中,雖然為人們看過(guò)、聽(tīng)過(guò),甚至經(jīng)歷過(guò),但總是處于一種無(wú)意識(shí)的壓抑或者無(wú)感覺(jué)的缺失狀態(tài),也只有在特殊情況下,才可能被人們發(fā)現(xiàn)或者意識(shí)到。這也許就是古語(yǔ)所言的“觸景生情”“觸物及人”,那些被人們壓抑的或者無(wú)感覺(jué)的東西,經(jīng)過(guò)某一空間中的物的觸發(fā),從而引起一段故事,陸游幾十年后重游沈園的著名詩(shī)話即是如此。人的夢(mèng)也是一種空間意識(shí)的轉(zhuǎn)化形式,在夢(mèng)中,會(huì)像電影一樣將某一故事在空間中展現(xiàn)出來(lái)。如前蘇聯(lián)電影《伊萬(wàn)的童年》中,少年伊萬(wàn)在田地、森林、沙灘玩耍以及曬人的陽(yáng)光,挑水而來(lái)的母親,之后母親被飛機(jī)炸死井旁的畫(huà)面經(jīng)常出現(xiàn)在他的夢(mèng)里。再如《拯救大兵瑞恩》是以倒敘的回憶的形式引入整個(gè)電影的,影片開(kāi)始于一位老人(被救回來(lái)的瑞恩)在墓碑前的回憶,從而切入整部電影,尤其是開(kāi)始的諾曼底登陸戰(zhàn)役的描繪,是空間敘事的絕佳例子。影像本身具有空間性,其敘事比起線性的時(shí)間敘事在空間方面更具有優(yōu)勢(shì),但是,時(shí)間并非不能進(jìn)行空間敘事,時(shí)間往往運(yùn)用其連續(xù)性將空間中發(fā)生的時(shí)間描述出來(lái),從而具有了空間形式,尤其是針對(duì)于本身就具有空間性特色的戰(zhàn)爭(zhēng)敘事而言。
在海明威的小說(shuō)《永別了,武器》中,在大量的人物對(duì)白中,盡管是按照先后的時(shí)間順序進(jìn)行的,但故事發(fā)生的地點(diǎn)隨著醫(yī)院等地方的變動(dòng),空間位置也在不停地轉(zhuǎn)換。隨著空間位置不停的轉(zhuǎn)換,時(shí)間反而被忽略了,只是白天、黑夜、季節(jié)等等模糊的展現(xiàn),尤其在描述戰(zhàn)斗的場(chǎng)面時(shí),這種空間形式的表現(xiàn)就十分明顯,下面就以小說(shuō)中亨利負(fù)傷后的敘述部分為例加以分析。
“地面已被炸裂,有一塊炸裂的木椽就在我頭前。我頭一顫動(dòng),聽(tīng)見(jiàn)有人在哭。我以為有人在哀叫。我想動(dòng),但是動(dòng)不了。我聽(tīng)見(jiàn)對(duì)岸和沿河河岸上的機(jī)槍聲和步槍聲,有一聲響亮的濺水聲,我看見(jiàn)一些照明彈在往上升,接著炸裂了,一片白光在天上漂浮著,火箭也射上上去,還聽(tīng)見(jiàn)炸彈聲。這一切都是一瞬間的事,隨后我聽(tīng)見(jiàn)附近有人在說(shuō):‘我的媽啊,噢,我的媽啊!’我拼命拔,拼命扭,終于抽出了雙腿轉(zhuǎn)過(guò)身去摸摸他,原來(lái)是帕西尼,我一碰他,他便死命叫痛。他的兩腿朝著我,我在暗中和光中看出他兩條腿的膝蓋以上全給炸爛了”。⑧
顯然,語(yǔ)言只能遵循時(shí)間的先后順序來(lái)描述,但閱讀的時(shí)候,人們并不是將每一個(gè)字、句切開(kāi)來(lái)理解的,而是從整體出發(fā)來(lái)認(rèn)識(shí)作品的,上一片斷似乎有著時(shí)間順序,但是,在此時(shí)間的先后已經(jīng)不是本質(zhì)性問(wèn)題,而是文字排列必須如此,實(shí)際上,并非展開(kāi)了一幅幅以時(shí)間順序的動(dòng)作,而是此刻在空間中立體呈現(xiàn)的畫(huà)面。這些立體的含有一系列行動(dòng)的畫(huà)面就是故事的空間形式,是敘事在消失了的時(shí)間軸上組合上的一種空間表現(xiàn),是一種空間敘事。這類敘事在戰(zhàn)爭(zhēng)藝術(shù)作品里經(jīng)常會(huì)看到,其空間形式也很明顯,再如詹姆斯·瓊斯的二戰(zhàn)小說(shuō)《細(xì)紅線》中美國(guó)士兵比德在戰(zhàn)斗間隙碰巧撞見(jiàn)了一個(gè)日軍士兵的故事,比德在緊張之中竟然并沒(méi)有殺死敵人,顯得慌亂而又氣急敗壞,小說(shuō)這樣寫(xiě)道:
比德見(jiàn)日本兵還沒(méi)死,變得怒不可遏,哭著喊著滾到一邊抓住步槍,膝蓋著地,把步槍高舉過(guò)頭頂,然后猛地把刺刀捅進(jìn)日本兵的胸膛,幾乎穿透了。日本兵的身子一陣痙攣。他睜開(kāi)眼睛,恐懼茫然地瞪著比德,抬起雙手抓住胸前刺刀。⑨
同樣地,動(dòng)作的先后以及諸如“然后”等時(shí)間性詞語(yǔ)依然呈現(xiàn)著線性的發(fā)展順序,但空間維度卻在緊張地展開(kāi),一系列動(dòng)作性詞語(yǔ)以及對(duì)于動(dòng)作的詳細(xì)描述進(jìn)一步增強(qiáng)了空間形式的延展性、緊張性。“此刻”的“奇異性”使得時(shí)間被忽略了,或者隱匿了。單就空間形式的動(dòng)態(tài)性以及動(dòng)作的激烈程度而言,比起其它與歷史相關(guān)的題材的敘事作品多呈現(xiàn)靜態(tài)的空間形式來(lái),當(dāng)然,武俠或者其它的暴力為主題的作品應(yīng)該例外,這一方面,戰(zhàn)爭(zhēng)敘事更富有空間性,或者說(shuō),戰(zhàn)爭(zhēng)敘事會(huì)是空間敘事最典型的表現(xiàn)形式。而電影藝術(shù)中的戰(zhàn)爭(zhēng)呈現(xiàn)或者說(shuō)電影中的戰(zhàn)爭(zhēng)敘事是空間敘事最突出的表現(xiàn)形式的代表。如果說(shuō),在戰(zhàn)爭(zhēng)小說(shuō)中,時(shí)間形式表現(xiàn)得依然很明顯,故事有其時(shí)間上嚴(yán)格的先后順序,這也可能是文字不得不如此的問(wèn)題,而并非敘事的問(wèn)題。而在戰(zhàn)爭(zhēng)電影中,這一方面已經(jīng)有所突破,更注重空間形式,即使在小說(shuō)中,時(shí)間的優(yōu)勢(shì)也在打破,至少有部分作家越來(lái)越注重空間敘事,如法國(guó)新小說(shuō)派作家克勞德·西蒙的《弗蘭德公路》。該小說(shuō)描繪了1940 年春季法軍被德軍擊敗后, 在法國(guó)北部弗蘭德公路上潰退的情形。但正如作者所說(shuō)那樣,“把現(xiàn)代小說(shuō)當(dāng)作現(xiàn)代繪畫(huà)來(lái)看”。⑩作者在小說(shuō)中把現(xiàn)實(shí)、夢(mèng)境、回憶、想象、幻覺(jué)、潛意識(shí)等都融入其中,使小說(shuō)具有繪畫(huà)一樣的共時(shí)性和多樣性的特點(diǎn),不再以時(shí)間形式作為敘事的線索,而是打破時(shí)間感,以充滿繪畫(huà)般的空間感描述千變?nèi)f化的世界。不像傳統(tǒng)小說(shuō),《弗蘭德公路》沒(méi)有完整而統(tǒng)一的故事情節(jié),而是以空間特征極其明顯的場(chǎng)景組合替代了情節(jié)的延續(xù)發(fā)展,甚至以空間藝術(shù)代替時(shí)間形式來(lái)表現(xiàn)戰(zhàn)爭(zhēng)的殘酷、失望,丑惡和荒謬。
二、境在像外:作為空間敘事的戰(zhàn)爭(zhēng)
敘事的“虛”與“實(shí)”如上所述,戰(zhàn)爭(zhēng)敘事以其最富有動(dòng)態(tài)性和極端性的空間方式呈現(xiàn)了戰(zhàn)爭(zhēng)的空間形式,從而成為空間敘事的典型。既然敘事表現(xiàn)為空間形式,其必然是以視覺(jué)化的形式展現(xiàn)在受眾面前,不管是以文字形式,還是以圖像形式,也不論其是平面的,還是立體的。圖像的形式是直觀的,直接將形象呈現(xiàn)于受眾眼前,而文字則是以故事空間和話語(yǔ)空間等形式構(gòu)造的敘事空間來(lái)表現(xiàn)這一特征的,是一種構(gòu)建的空間圖像,不像繪畫(huà)或者其它材料如雕刻用到的銅、石塊等構(gòu)成的圖像那樣直觀,或者本身就是一個(gè)實(shí)體。
所以,對(duì)于戰(zhàn)爭(zhēng)敘事而言,空間敘事中,所謂“實(shí)”對(duì)于戰(zhàn)爭(zhēng)繪畫(huà)、雕刻等以物質(zhì)性材料來(lái)說(shuō),就是主體的形狀,輪廓包圍的空間,這是一種物質(zhì)性空間。對(duì)于戰(zhàn)爭(zhēng)文學(xué)藝術(shù)而言,則是通過(guò)文字呈現(xiàn)的故事空間以及意蘊(yùn)空間,是一種意象空間。戰(zhàn)爭(zhēng)電影綜合了二者的特征,雖然不像雕刻那樣具有實(shí)體性的物理空間,但將其物質(zhì)性的一面加以借用,又利用了文字、音樂(lè)、戲劇等藝術(shù)的長(zhǎng)處,能夠進(jìn)一步將戰(zhàn)爭(zhēng)敘事的特性及戰(zhàn)爭(zhēng)的本質(zhì)展現(xiàn)出來(lái)。不論是物質(zhì)性空間還是通過(guò)故事空間等營(yíng)造的意象空間,這種“實(shí)”構(gòu)造了敘述的時(shí)間即故事,也為將敘事引向形而上的意蘊(yùn)提供了物質(zhì)基礎(chǔ)。而后者,則是戰(zhàn)爭(zhēng)敘事所謂的“虛”,這種“虛”,就是戰(zhàn)爭(zhēng)敘事在“實(shí)”的基礎(chǔ)上構(gòu)建的審美空間,這一空間敘事以戰(zhàn)爭(zhēng)的極端性作為依托,以人的生命、情感、道德等為代價(jià),呈現(xiàn)出的審美景觀和審美判斷,“虛”依托“實(shí)”建立了審美意義上的空間。“實(shí)”創(chuàng)造了“虛”,而“虛”卻又創(chuàng)造力“實(shí)實(shí)在在”的內(nèi)涵。這一內(nèi)涵是將人置于極端的情景之下進(jìn)行觀照之后產(chǎn)生的,既有審美意義,也有道德的價(jià)值,更可能是對(duì)人以及人們生存的世界以及存在本身的審美的和形而上的思考。這一點(diǎn)是其它題材所不能達(dá)到的廣度和深度,這也正是戰(zhàn)爭(zhēng)敘事本質(zhì)所在。如清代戴熙在《習(xí)苦齋畫(huà)絮》中這樣總結(jié)到:“畫(huà)在筆墨處,畫(huà)之妙在無(wú)筆墨之處”。筆墨是“實(shí)”,通過(guò)筆墨之“實(shí)”構(gòu)建的景象、意象,達(dá)到“無(wú)筆墨之處”的“妙”的境界便是“虛”。笪重光在《畫(huà)荃》中也談到了“虛”與“實(shí)”的關(guān)系問(wèn)題。“空本難圖,實(shí)景清而空景觀。神無(wú)可繪,真境逼而神境生,位置相戾,有畫(huà)處多屬敖疣,虛實(shí)相生,無(wú)畫(huà)處畢成妙境”。審美意境以及心靈的產(chǎn)生,就在虛實(shí)相生相融的剎那,即所謂“神境”“妙境”的產(chǎn)生。使得受眾在欣賞或者接受的過(guò)程中攝取原來(lái)作品之魂魄,在虛實(shí)相生的藝術(shù)空間之外別構(gòu)一個(gè)靈奇境界。
以圖像敘事而言,有單幅圖像戰(zhàn)爭(zhēng)空間敘事和系列圖像或全景式圖像戰(zhàn)爭(zhēng)空間敘事。一般來(lái)看,敘事時(shí)間既可以是一個(gè)時(shí)期,也可以是一段時(shí)間,還可以是剎那間,即詹姆遜所言的“此刻”,但在藝術(shù)作品中,離開(kāi)了空間的呈現(xiàn),這種時(shí)間依然沒(méi)有意義。而且,對(duì)于接受者而言,尤其是在戰(zhàn)爭(zhēng)敘事中,具有關(guān)鍵性意義或者決定作品的效果的,往往是那些“最富于孕育性的頃刻”描述的故事斷片,即“此刻”的展現(xiàn),而不是作品整個(gè)敘事時(shí)間發(fā)生的所有事件,當(dāng)然,并不是說(shuō),整個(gè)故事并不重要,因?yàn)椋@一斷片最終要回到整體空間上來(lái)看,否則,也只是一個(gè)殘片而已,這一方面,在除過(guò)單幅戰(zhàn)爭(zhēng)繪畫(huà)和雕刻之外的體裁方面,都具有突出的表現(xiàn)。就其“最富于孕育性的頃刻”點(diǎn)敘事特征來(lái)看,一部作品所呈現(xiàn)的戰(zhàn)爭(zhēng)敘事可以看作是由一幅幅單個(gè)圖像敘事構(gòu)成的連續(xù)的系列。最簡(jiǎn)單的就是單幅的戰(zhàn)爭(zhēng)繪畫(huà)、雕刻或者雕塑,以及其它體裁如小說(shuō)、詩(shī)歌、戲劇、電影等中的具有點(diǎn)敘事特征的片段,如前所言,這一類戰(zhàn)爭(zhēng)敘事盡管強(qiáng)調(diào)了瞬間的特征,但最后的效果則要回到整部作品所創(chuàng)造的整體空間中才能體現(xiàn)出來(lái)。也就是說(shuō),在這一時(shí)空關(guān)系中,虛與實(shí)相互襯托,輝映成趣,營(yíng)造一個(gè)意蘊(yùn)空間。
藝術(shù)作品的戰(zhàn)爭(zhēng)敘事,其形式上表現(xiàn)的“實(shí)”,一是語(yǔ)言文字及其描繪的景象,如小說(shuō)、詩(shī)歌中用文字描繪的戰(zhàn)爭(zhēng)場(chǎng)面、人及物的描寫(xiě)等;二是指即繪畫(huà)、雕刻以及電影中呈現(xiàn)在畫(huà)面、銀幕上的各種切實(shí)可感的真實(shí)存在。“虛”一方面是指繪畫(huà)中的虛空之處,雕刻中留出來(lái)的空間,它是物理形式存在的虛或者空,如戈雅的《1808年5月3日的槍殺》這幅畫(huà)作中的背景部分中那片黑暗的天空。另一方面則是指各種藝術(shù)形式的戰(zhàn)爭(zhēng)敘事所表現(xiàn)出來(lái)的含有抽象意義的意蘊(yùn)、藝境或者情致。戰(zhàn)爭(zhēng)電影本身就是動(dòng)態(tài)的、空間性極強(qiáng)的藝術(shù),這類戰(zhàn)爭(zhēng)敘事更多的側(cè)重于通過(guò)“實(shí)”產(chǎn)生的意蘊(yùn)。“實(shí)”必須落實(shí)在形象刻畫(huà)的物理意義層面,也就是作品中的人物、場(chǎng)景、景象或者意象及故事等的延續(xù)與發(fā)展上,否則,“虛”則無(wú)以憑借。“虛”是包含有物理形式產(chǎn)生的物象之后看不見(jiàn)、摸不著的經(jīng)由想象加工的意蘊(yùn)空間。這一意蘊(yùn)空間,是包含著意象與情感等等范疇的審美及認(rèn)知判斷的綜合體,是一種詩(shī)性經(jīng)驗(yàn)、認(rèn)知,而不是純粹的形而上的抽象概念。
看,是人的直覺(jué),是人最為本己的認(rèn)識(shí)事物的方式。具體到各個(gè)藝術(shù)門類,不論是小說(shuō)、詩(shī)歌、繪畫(huà)還是電影,“看”至始至終都是一種最基本的方式,而且,“看”最終能夠在受眾的心中形成對(duì)所看之物的體驗(yàn)和認(rèn)識(shí),它既能夠完整地保持事物的形象,又使之是其所是,盡管這一事物已經(jīng)并非原來(lái)之事物,是一種在原來(lái)事物之上的意象或者鏡像。這一意象或者鏡像的特征在于,它使得事物能夠得以完整地顯現(xiàn)自身,并引發(fā)受眾的最為本初的發(fā)自內(nèi)心的真切感受。所以,不管哪種藝術(shù)門類,都能借“看”這一方式使事物及其內(nèi)涵得以顯現(xiàn),并使保持在事物的“本體”、“本性”,或者“本質(zhì)”得以呈現(xiàn),而且同時(shí)又能夠引起受眾對(duì)它們真正的理解和認(rèn)識(shí)。因此,在最終的審美旨趣或者意義探求上,不論是基于文字的形構(gòu),還是基于圖像的構(gòu)建的戰(zhàn)爭(zhēng)空間敘事,在此殊途而同歸。
西方有人曾經(jīng)認(rèn)為,敘寫(xiě)戰(zhàn)爭(zhēng)的最具有代表性的藝術(shù)門類中,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最有代表性的是詩(shī)歌,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是小說(shuō),而越南戰(zhàn)爭(zhēng)則是電影。它們的共同點(diǎn)都在于都如實(shí)地刻畫(huà)了戰(zhàn)爭(zhēng)令人驚懼的一面,給人們以深刻的啟示。在這些體裁中,針對(duì)戰(zhàn)爭(zhēng)敘事,恰恰最不能寫(xiě)“實(shí)”的,是詩(shī)歌,最不能呈現(xiàn)“虛”的一面的,是電影,小說(shuō)居于其間,小說(shuō)既有故事的延續(xù),又有場(chǎng)景、景象的描繪,比起詩(shī)歌與電影而言,既可以寫(xiě)“實(shí)”,如把戰(zhàn)爭(zhēng)的場(chǎng)面刻繪的惟妙惟肖,又可以寫(xiě)“虛”,它可以岔開(kāi)戰(zhàn)爭(zhēng)不談,敘寫(xiě)別的內(nèi)容,甚至看似離開(kāi)了戰(zhàn)爭(zhēng)敘事的主題,實(shí)則相反,虛而實(shí),實(shí)而虛。戰(zhàn)爭(zhēng)繪畫(huà)與雕刻甚至建筑有些與小說(shuō)相似,雖然更多的則是呈現(xiàn)于人們眼前的“實(shí)”的物理存在,實(shí)則虛實(shí)相間,“虛”借“實(shí)”以闡發(fā)意義。下面就以詩(shī)歌和電影為例,來(lái)闡述戰(zhàn)爭(zhēng)敘事虛與實(shí)相互映襯之下呈現(xiàn)的審美意蘊(yùn)空間。
“華滋華斯曾言,‘詩(shī)歌是強(qiáng)烈感情的自然流露’。似乎不存在一個(gè)比戰(zhàn)爭(zhēng)更能讓人產(chǎn)生強(qiáng)烈感情的東西:希望與恐懼、狂喜與羞辱、憎恨——不僅僅是對(duì)敵人的憎恨,還包括對(duì)將軍、政治家、戰(zhàn)爭(zhēng)販子,熱愛(ài)——也不僅僅是對(duì)戰(zhàn)友的愛(ài),還包括留在后方的女人和孩子、對(duì)祖國(guó)(時(shí)常)和事業(yè)(偶爾)的熱愛(ài)”。
除此之外,戰(zhàn)爭(zhēng)詩(shī)歌還表達(dá)了戰(zhàn)場(chǎng)上的空虛、寂寞與生命被耗費(fèi)的無(wú)聊感的同時(shí),也對(duì)現(xiàn)代社會(huì)以及人的命運(yùn)進(jìn)行深入的思考,對(duì)現(xiàn)代戰(zhàn)爭(zhēng)及人的本性進(jìn)行深入的反思。正如上述,詩(shī)歌往往以言情見(jiàn)長(zhǎng)(敘事詩(shī)除外),尤其是短小的篇章,詩(shī)人們不可能在如此有限的篇幅內(nèi)描繪整個(gè)戰(zhàn)爭(zhēng),講述故事,而是以精簡(jiǎn)的語(yǔ)言,通過(guò)戰(zhàn)場(chǎng)的景觀描繪,抒發(fā)自己的感情,而且,基本上,戰(zhàn)爭(zhēng)詩(shī)歌的作者往往就是戰(zhàn)士,有些詩(shī)歌直接就是戰(zhàn)場(chǎng)上或者戰(zhàn)壕里的產(chǎn)物,如意大利詩(shī)人翁加雷蒂不少詩(shī)歌,就是寫(xiě)于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戰(zhàn)壕里。
首先來(lái)看法國(guó)超現(xiàn)實(shí)主義詩(shī)人本雅明·佩雷(Benjamin Péret)的《殘疾人短歌》
殘疾者短歌
給我,你的胳膊
替換我的腿
讓老鼠,噬嚙吧
在凡爾登——
在凡爾登——
我,吃掉了多只老鼠
并不能,還回我的腿
我,獲得了十字勛章
再加,一條木腿
再加,一條木腿
要想在這首詩(shī)歌里尋找敘事時(shí)間,似乎很難,因?yàn)樵?shī)歌中并沒(méi)有明顯的時(shí)間語(yǔ)言。盡管如此,詩(shī)歌依然言說(shuō)著一個(gè)殘疾士兵的簡(jiǎn)短的故事:在凡爾登發(fā)生的戰(zhàn)斗中,一個(gè)饑餓得在戰(zhàn)壕里只能吃老鼠的士兵,丟掉了一條腿,榮獲了法國(guó)英勇十字勛章。敘事空間在詩(shī)歌里有所交代,即故事空間——凡爾登戰(zhàn)役的戰(zhàn)場(chǎng)。從敘述視角看,全詩(shī)以第一人稱“我”來(lái)統(tǒng)領(lǐng),“我”敘說(shuō)我的故事。就整首詩(shī)歌來(lái)看,敘事很簡(jiǎn)單。詩(shī)歌中交代的這些內(nèi)容以及文字,便構(gòu)成了整個(gè)詩(shī)歌的“實(shí)”,即敘事空間,然而,閱讀并不能就此完結(jié),而是走向作品之外,這種外也就是詩(shī)歌語(yǔ)句、語(yǔ)氣、語(yǔ)調(diào)等營(yíng)造的意蘊(yùn)空間,進(jìn)而通過(guò)這一意蘊(yùn)空間延伸為空間敘事。在這首詩(shī)歌中,表現(xiàn)為詩(shī)歌語(yǔ)句、語(yǔ)氣、語(yǔ)調(diào)等營(yíng)造的意蘊(yùn)空間,一種情致。簡(jiǎn)單的重復(fù)給整個(gè)詩(shī)歌增添一絲感傷的氣息,勛章與一條木腿的暗比表達(dá)了一種無(wú)奈之情,也是一種復(fù)雜的酸楚感受。一方面是來(lái)自官方的榮譽(yù),另一方面是個(gè)人的悲哀與不幸。而戰(zhàn)斗中吃老鼠和被老鼠吃的意象折射出戰(zhàn)爭(zhēng)的殘酷,也更加折射出人性的悲哀。詩(shī)歌在一種低緩的、沉重的語(yǔ)調(diào)中,在一種近乎酸楚的暗諷的悲哀中結(jié)束。這些,都是詩(shī)歌中“虛”所構(gòu)建的內(nèi)容,借語(yǔ)言描繪之實(shí),進(jìn)入一種復(fù)雜的象外之象的情感狀態(tài),或者情致。從而虛與實(shí)相得益彰,將戰(zhàn)爭(zhēng)的殘酷、人性的悲哀訴諸于前。
戰(zhàn)爭(zhēng)電影以空間寫(xiě)“實(shí)”見(jiàn)長(zhǎng),展現(xiàn)系列動(dòng)態(tài)的空間過(guò)程是其最大的特色,尤其是戰(zhàn)爭(zhēng)的動(dòng)態(tài)發(fā)展的過(guò)程,將戰(zhàn)爭(zhēng)的極端性呈現(xiàn)于人們眼前,從而給人以逼真的效果,這都是“實(shí)”的功夫。如《拯救大兵瑞恩》開(kāi)始的諾曼底登陸戰(zhàn),即是如此。其再現(xiàn)的真實(shí)戰(zhàn)爭(zhēng)場(chǎng)面,逼真的效果令人們將其冠以有史以來(lái)最逼真的戰(zhàn)爭(zhēng)片之一的稱號(hào),雖然美國(guó)電影協(xié)會(huì)將該片定為“極度渲染戰(zhàn)爭(zhēng)暴力”的影片,但許多參加過(guò)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老兵給予了影片極高的評(píng)價(jià),認(rèn)為它是“最真實(shí)反映二戰(zhàn)的影片”,尤其是電影開(kāi)始部分長(zhǎng)達(dá)26分鐘之久的諾曼底登陸的恢宏場(chǎng)面。這一場(chǎng)面,也是一場(chǎng)景觀,一段典型的空間敘事,時(shí)間依然存在,但時(shí)間已經(jīng)隱匿了起來(lái),受眾在緊張甚至震驚的心情中隨著空間的推進(jìn),了解這一驚心動(dòng)魄的敘事過(guò)程。登陸艇掀起重重海浪行進(jìn)著,士兵們緊張地抓著艇沿,有的吐了起來(lái),有的大口大口地夸張性地嚼著口香糖,有的不停地祈禱著。當(dāng)靠近海岸打開(kāi)艙門登陸時(shí),德軍的子彈無(wú)情地掃射過(guò)來(lái),成群成群的美國(guó)士兵來(lái)不及走出艙門就倒了下去,跳到水里的,有被擊中而亡的,有淹死的;上岸的士兵們倉(cāng)皇地尋找著能夠躲避的地方,一名失掉了手臂的士兵來(lái)回走著,接著就彎腰撿起斷掉的手臂,喊著去找醫(yī)護(hù)兵。米勒救出戰(zhàn)友,拖著往前走,這時(shí)候,一顆炮彈在旁邊炸開(kāi),米勒到了下去,當(dāng)他醒來(lái)時(shí),抓著戰(zhàn)友繼續(xù)走,當(dāng)他意識(shí)到什么的時(shí)候,一回頭,戰(zhàn)友的身體只剩下血淋林的上半截拖在自己的手里。而旁邊一名受傷倒地的士兵大聲地叫喊著“媽媽”,他的腹部已經(jīng)炸開(kāi),腸子遺落滿地。當(dāng)沖到戰(zhàn)壕邊的米勒上尉抓著通訊兵再次給上級(jí)報(bào)告時(shí),抓過(guò)來(lái)的是一張面部幾乎被掏空的骷髏一樣的尸體。戰(zhàn)斗結(jié)束的時(shí)候,米勒看了看整個(gè)海灘,海水里、沙灘上到處都是橫七豎八歪躺著的尸體,海水也是殷紅的一片。詹姆遜所講到的“此刻”的“奇異性”的美,就是時(shí)間消匿,空間主宰著敘事,莫過(guò)于此。
整個(gè)過(guò)程緊張、刺激、驚懼而恐怖,既體現(xiàn)了戰(zhàn)爭(zhēng)敘事極端性的一面,也突出地表現(xiàn)了戰(zhàn)爭(zhēng)敘事作為空間敘事的典型形式的一面:依賴于空間形式進(jìn)行敘事。這也是戰(zhàn)爭(zhēng)電影敘事“實(shí)”的一面,以極端的動(dòng)作形態(tài)和畫(huà)面的更迭變化來(lái)推動(dòng)整個(gè)敘事,詹姆遜所言的時(shí)間終結(jié),在這里也體現(xiàn)得很明顯,“此刻”或者點(diǎn)敘事成為敘事的重點(diǎn)。但影片中也表現(xiàn)了敘事“虛”的一面,如登陸艇上士兵們緊張而不安的表現(xiàn),尤其是最后的鏡頭落在一名爬著死去的士兵的寫(xiě)著瑞恩的名字背包上,突兀地插入一筆,雖出人意外,卻又在整個(gè)敘事之中,為后面的敘事留下伏筆。另外,“虛”的空間還存在于受眾觀看時(shí)的意象空間之中,存在于他們的對(duì)于“看”的領(lǐng)悟當(dāng)中,通過(guò)觀看,人們?cè)诰o張、刺激甚至恐怖中領(lǐng)悟到戰(zhàn)爭(zhēng)的本質(zhì)和生命的脆弱,從空間敘事的“實(shí)”進(jìn)入“虛”的領(lǐng)悟,從“看”進(jìn)入到審美觀照、審美認(rèn)知。
這是激烈的戰(zhàn)斗場(chǎng)面呈現(xiàn)的空間敘事形式,而對(duì)于并沒(méi)有激烈的戰(zhàn)爭(zhēng)場(chǎng)面的空間敘事,其“虛”的一面更為明顯,而且闡發(fā)的意義更為廣泛而深刻,它不只是反映了戰(zhàn)爭(zhēng)的殘酷的一面,也反映更為廣泛的主題,諸如人類社會(huì)、人的本質(zhì)、宗教、政治等。美國(guó)戰(zhàn)爭(zhēng)電影《現(xiàn)代啟示錄》就是如此。
電影是空間敘事的典型形式,而戰(zhàn)爭(zhēng)電影尤其如此,其極端的動(dòng)態(tài)效果推進(jìn)著整個(gè)敘事過(guò)程,敘事時(shí)間只是呈現(xiàn)為白天或者季節(jié)等概念的無(wú)意識(shí)的交替,成為背景而已。插敘在這部電影中。表現(xiàn)得極為突出,盡管它也表現(xiàn)出一定的動(dòng)態(tài)的空間形式,是“實(shí)”的體現(xiàn)。但插敘往往是敘事主題的偏出,甚至與主題無(wú)關(guān),所以,其往往呈現(xiàn)為“虛”的一面,如該電影中滑水的情景,上校為開(kāi)辟滑水的理想場(chǎng)地而轟炸越軍據(jù)點(diǎn),甚至在轟炸中也用高音喇叭播放著瓦格納的音樂(lè),在蘭斯他們偷走上校的滑板時(shí),他乘著戰(zhàn)斗機(jī)追尋的情景;威拉德上尉一行碰到的花花公子女郎慰問(wèn)軍隊(duì)的表演,以及后面再次碰到她們的事件;威拉德在法國(guó)種植園主家迷蒙的夜晚與一位寡婦的浪漫情懷,一路上與越南老百姓的沖突,奇異的異國(guó)風(fēng)景,他們到達(dá)目的地掛滿尸體的樹(shù)枝、地上樹(shù)立的人頭等等,都是以空間畫(huà)面展開(kāi)的形式展現(xiàn)“虛”的一面,這些表面看起來(lái)與威拉德的任務(wù)及電影的敘事主題沒(méi)有多少關(guān)系,但卻另有深意,即更深層次地展現(xiàn)了戰(zhàn)爭(zhēng)令人恐怖的一面,甚至人類社會(huì)、人本身等等本質(zhì)的一面。
正是這種虛實(shí)交錯(cuò)的空間敘事形式從而使得主題更為豐滿,將受眾引入到想象開(kāi)拓的意象空間,從而在這一意蘊(yùn)中認(rèn)識(shí)戰(zhàn)爭(zhēng)、理解戰(zhàn)爭(zhēng),甚至認(rèn)識(shí)人類社會(huì),認(rèn)識(shí)人的存在本身。而戰(zhàn)爭(zhēng)的荒誕與虛無(wú)感,人的生存的無(wú)意義感都依賴于這一虛實(shí)相間的敘事之中。上校不是為了戰(zhàn)爭(zhēng)而進(jìn)行戰(zhàn)斗,而是為了開(kāi)辟滑水的理想地點(diǎn),戰(zhàn)爭(zhēng)自古以來(lái)就是人類社會(huì)的“宏大敘事”,在這里也只不過(guò)是隨心所欲的玩具罷了,但這一玩具的代價(jià)未免太大,畢竟,一些人是要付出寶貴的生命。花花公子女郎前后命運(yùn)的對(duì)比,不僅僅揭示了戰(zhàn)爭(zhēng)的冷酷和恐怖,也揭示著普通人卷入戰(zhàn)爭(zhēng)的可悲命運(yùn),戰(zhàn)爭(zhēng)就是一架著魔的噬人的怪獸,沒(méi)有人能逃脫它的魔掌。威拉德上尉法國(guó)種植園的浪漫一夜,那位寡婦在迷蒙的夜色下鬼魅般的身體,在死的主題之中,膠著生的本能渴望,但生的狂歡又何嘗不是死的慶典。戰(zhàn)爭(zhēng)的荒謬感、生與死、人的命運(yùn)的不可琢磨等等正是通過(guò)這一意蘊(yùn)空間得到了闡發(fā)。
《莊子·天地》篇中講到一個(gè)故事,“黃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化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呂惠卿說(shuō):“象則非無(wú),罔則非有,有白敫不昧,玄珠之所以得也”。
在這則故事中,很多人都理解為要得“道”,不能依靠智識(shí),也不能依靠視覺(jué),而是要依賴于象罔,只有在象罔的觀照下,才可能達(dá)到真正的境界。但人們忽略了在觀照之中,不僅僅是得“道”,在通往“道”的過(guò)程中,存在的審美環(huán)節(jié)。在對(duì)于藝術(shù)作品的觀照之中,并不是像哲思一樣,直達(dá)目的,而是在審美愉悅的基礎(chǔ)上,在再生的審美境界中得“道”。所以,戰(zhàn)爭(zhēng)敘事亦是如此,只有在對(duì)戰(zhàn)爭(zhēng)敘事的審美意象構(gòu)成的審美空間的觀照之中,達(dá)成對(duì)于戰(zhàn)爭(zhēng)以及人的存在的本質(zhì)性認(rèn)識(shí)。
另一方面,從符號(hào)學(xué)的角度看,所謂“實(shí)”,實(shí)際上也是文字或者色彩、線條、石塊等組成的一個(gè)或多個(gè)符號(hào),按照符號(hào)分析的方法,“一個(gè)符號(hào)的意義本身并不完整,甚至不存在于其本身之內(nèi),而是以這種或那種形式散布于所有其它符號(hào)之中,而且這種意義跨越其他符號(hào)的散布是無(wú)限的”。這些符號(hào)是真實(shí)的,可視的,在雕刻或者建筑物中,也是可以觸摸的,但符號(hào)所傳達(dá)出來(lái)的意義,跨越了符號(hào)的界限,其意義是無(wú)限的,散布的,進(jìn)入到符號(hào)之外的“虛”的空間,即符號(hào)之外的看不見(jiàn)、摸不著的甚至只可意會(huì)而不可言傳的意蘊(yùn)空間。
所以說(shuō),戰(zhàn)爭(zhēng)敘事的空間形式,是一種從物理空間到審美心理空間的轉(zhuǎn)化的空間敘事過(guò)程。在這一過(guò)程中,虛與實(shí)相互對(duì)立而又統(tǒng)一于藝術(shù)作品之中,達(dá)到虛實(shí)相生,形成豐富的藝術(shù)表現(xiàn)力和深厚的審美內(nèi)涵,是一種傳達(dá)超越性精神境界的詩(shī)性敘事。
①史蒂芬·霍金《時(shí)間簡(jiǎn)史》,湖南科技出版社,2001年,第13頁(yè)。
②James H. Pickering & Jeffrey D. Hoeper,Literature, New York: Macmillan, 1982, p.28.
③米克·巴爾著,譚君強(qiáng)譯《敘述學(xué):敘事理論導(dǎo)論》,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2003年版,第258頁(yè)。
④(挪威)諾伯格·舒爾茲著,尹培桐譯《存在·空間·建筑》,中國(guó)建筑工業(yè)出版社,1990年版,第1頁(yè)。
⑤馬賽爾·馬爾丹:《電影語(yǔ)言》何振淦譯,中國(guó)電影出版社,1980年版,第185頁(yè)。
⑥W. J. T. Mitchell, Spatial Form in Literature, Critical Inquiry6 (1980), p.548.
⑦(法)拉康著,褚孝泉譯《拉康選集》,三聯(lián)書(shū)店,2001年版,第170頁(yè)。
⑧海明威著,林疑今譯《永別了,武器》,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頁(yè)。
⑨[美]詹姆斯·瓊斯著,姚乃強(qiáng)等譯《細(xì)紅線》,譯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145頁(yè)。
⑩見(jiàn)孫恒《的讀解:繪畫(huà)的結(jié)構(gòu)》,《外國(guó)文學(xué)評(píng)論》,1991年第1期。
[清]戴熙《習(xí)苦齋畫(huà)絮》,見(jiàn)俞劍華編著《中國(guó)畫(huà)論類編(下)》,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1986年,第996頁(yè)。
(清)笪重光《畫(huà)荃》,見(jiàn)葉郎主編《中國(guó)歷代美學(xué)文庫(kù)·清代卷(中)》,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7頁(yè)。
Jon Stallworthy: The Oxford Book of War Poet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xix.

預(yù)計(jì)1個(gè)月內(nèi)審稿 部級(jí)期刊
中國(guó)機(jī)械工業(yè)聯(lián)合會(huì)主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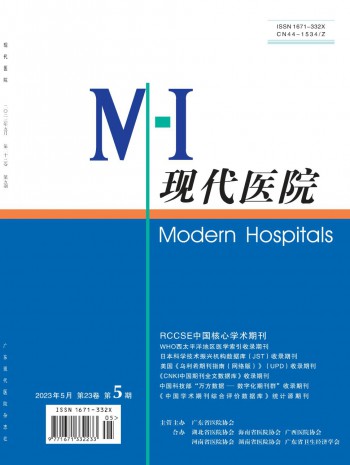
預(yù)計(jì)1個(gè)月內(nèi)審稿 省級(jí)期刊
廣東省醫(yī)院協(xié)會(huì)主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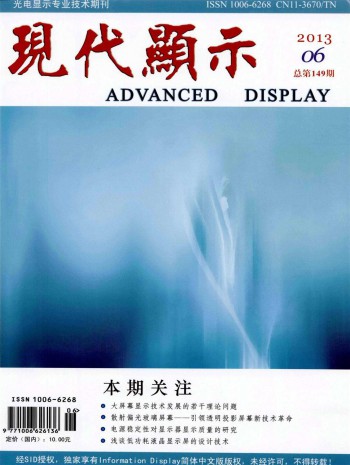
預(yù)計(jì)1個(gè)月內(nèi)審稿 省級(jí)期刊
北京市經(jīng)濟(jì)和信息化委員會(huì)主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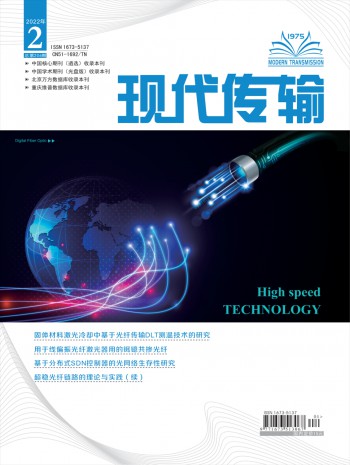
預(yù)計(jì)1個(gè)月內(nèi)審稿 部級(jí)期刊
信息產(chǎn)業(yè)部主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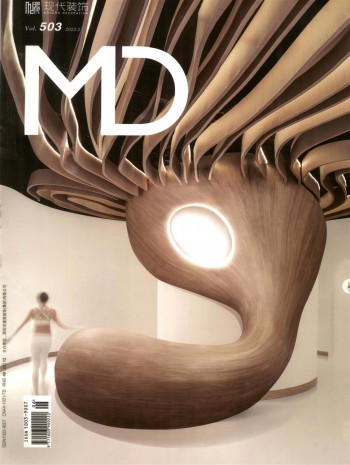
預(yù)計(jì)1個(gè)月內(nèi)審稿 省級(jí)期刊
深圳市建筑裝飾(集團(tuán))有限公司主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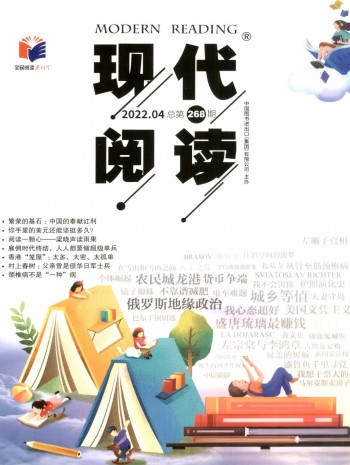
預(yù)計(jì)1個(gè)月內(nèi)審稿 部級(jí)期刊
中國(guó)出版集團(tuán)公司主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