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shí)間:2023-08-24 17:02:26
引言:易發(fā)表網(wǎng)憑借豐富的文秘實(shí)踐,為您精心挑選了九篇古代法律條文范例。如需獲取更多原創(chuàng)內(nèi)容,可隨時(shí)聯(lián)系我們的客服老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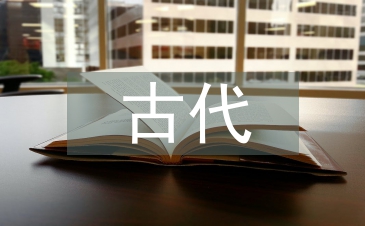
一個(gè)國(guó)家若想實(shí)現(xiàn)長(zhǎng)久的發(fā)展并保持一定的繁榮程度,健全的法律制度是不可或缺的,它可以為國(guó)家的長(zhǎng)治久安提供強(qiáng)有力的保障,只有社會(huì)穩(wěn)定了,其他社會(huì)事業(yè)才能發(fā)展。當(dāng)前,我國(guó)的法制建設(shè)正在不斷發(fā)展和進(jìn)步,不過還是有許多需要改進(jìn)和完善的地方。法家是先秦諸子中的主要派系之一,他們對(duì)法律最為重視,他們最主要也是對(duì)人類社會(huì)影響最為深重的主張就是以法治國(guó),突出法律這種國(guó)家的強(qiáng)制性工具在社會(huì)統(tǒng)治中的絕對(duì)準(zhǔn)繩地位。韓非子作為我國(guó)古代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雖然他所宣揚(yáng)的法制思想的社會(huì)背景有別于如今的社會(huì)背景,但我們還是可以從中看到許多值得我們當(dāng)今社會(huì)學(xué)習(xí)和借鑒的地方,我們可以去偽存真,汲取其中的精華來為我們社會(huì)主義法制建設(shè)服務(wù)。
韓非子(前281-前233),戰(zhàn)國(guó)末期韓國(guó)人,韓王室后裔,是我國(guó)古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政論家,法家的代表人物,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據(jù)相關(guān)文獻(xiàn)資料記載,韓非子雖然不擅言談,甚至有些口吃,但是其文采出眾,著作頗多,主要收集于《韓非子》這部作品中,主要就是關(guān)于法家思想的敘述,難能可貴的是韓非子的法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唯物主義色彩,這在我國(guó)古代諸多唯心主義流派林立的境況中獨(dú)樹一幟,并且一直延續(xù)到了現(xiàn)在,影響了我國(guó)幾千年的法制發(fā)展。
筆者經(jīng)過整理和分析一些資料文獻(xiàn),認(rèn)為韓非子法家思想的精華主要有以下幾點(diǎn):第一,第一次明確提出了法不阿貴的思想,這在我國(guó)是首創(chuàng),在春秋戰(zhàn)國(guó)時(shí)代當(dāng)時(shí)諸侯亂戰(zhàn)的背景下,雖有一定的時(shí)代局限性(當(dāng)時(shí)是封建主義專制時(shí)代),但這是對(duì)中國(guó)法制思想的重大貢獻(xiàn),對(duì)后世產(chǎn)生了極為深遠(yuǎn)的影響。不過其消極之處也顯而易見,那就是法不阿貴的對(duì)象不包括皇帝。第二,韓非子強(qiáng)調(diào)以刑上刑、嚴(yán)刑重罰,這對(duì)于治理當(dāng)時(shí)混亂的社會(huì)秩序是很有益處的,對(duì)于犯罪分子的震懾作用十分明顯。不過過于嚴(yán)厲的刑罰傷及了許多無辜百姓,甚至引起了一定范圍的民眾憤怒,沒有做到罪刑法定的原則。第三,法制的實(shí)施要以勢(shì)作為保證,所謂的勢(shì)實(shí)際上就是指政權(quán),也就是說法制的實(shí)施要想徹底必須要有強(qiáng)有力的政治權(quán)力作保障,穩(wěn)定而有力的政權(quán)是法制實(shí)施的前提。第四,還應(yīng)順應(yīng)時(shí)代的發(fā)展趨勢(shì),改革圖治,變法圖強(qiáng),縱觀世界歷史幾千年的發(fā)展,很多國(guó)家或者地區(qū)的繁榮昌盛都是從變法和改革開始的,比如我們的近鄰日本通過大化改新、明治維新兩次變法和改革,迅速實(shí)現(xiàn)了富國(guó)強(qiáng)兵的愿望。第五,韓非子將歷史的發(fā)展大致分為上古、中古、近古和當(dāng)今幾個(gè)階段,并且根據(jù)每一個(gè)時(shí)代的背景分而治之,具有一定的唯物主義思想色彩,也就是我們?nèi)缃裾軐W(xué)領(lǐng)域經(jīng)常所說的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一點(diǎn)是值得我們好好學(xué)習(xí)的。總體上來看,韓非子的法家思想就是集法、術(shù)、勢(shì)為一體的用法制治理國(guó)家的思想。
筆者認(rèn)為,韓非子的法家思想對(duì)我國(guó)法制建設(shè)還是有很多啟示的,總體來說是利大于弊。首先,應(yīng)繼續(xù)強(qiáng)調(diào)法不阿貴的思想,不過應(yīng)該天子犯法當(dāng)與庶民同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yàn)槿缃袷巧鐣?huì)主義法制社會(huì),不管是誰(shuí)違犯了法律,都應(yīng)受到相應(yīng)的刑罰,這是罪刑法定原則的具體體現(xiàn)。而韓非子所宣揚(yáng)的以刑上刑、嚴(yán)刑重罰思想顯然需要我們社會(huì)主義法制建設(shè)的改良,如今我國(guó)是依法治國(guó)和以德治國(guó)相結(jié)合,公民觸犯每一種刑罰都有法可依,也有法必依,但有法必依不等于量刑過重,要嚴(yán)格依據(jù)相關(guān)法律條文依法量刑。其次,應(yīng)效仿韓非子關(guān)于變法和改革的思想,順應(yīng)時(shí)代的發(fā)展大勢(shì),趨利避害,科學(xué)修改和完善以《刑法》為主的相關(guān)法律條文和法律制度。我國(guó)的《刑法》等法律條文經(jīng)過多年的不斷修正與完善,雖然還有一些滯后的地方,但是己經(jīng)取得了很多可喜的進(jìn)步。比如在關(guān)于死刑是否廢止的討論上,我國(guó)許多專家學(xué)者甚至一些公民都給出了自己認(rèn)為合理的建議,這實(shí)際上是我國(guó)大力普及社會(huì)主義法制觀念的結(jié)果。給我們的啟示是要不斷改革和完善《刑法》等法律條文中不符合或者落后于我國(guó)社會(huì)主義法制建設(shè)的部分。最后,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法律條文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我國(guó)的社會(huì)主義法制建設(shè)是一項(xiàng)艱巨而長(zhǎng)久的工程,在具體實(shí)施過程中會(huì)遇到許多問題,我們應(yīng)該效仿韓非子分而治之的思想,在法制建設(shè)過程中應(yīng)該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能拘泥于固定的法律條文,要靈活將法制與法治相結(jié)合,以保證國(guó)家的長(zhǎng)治久安和繁榮穩(wěn)定。
韓非子的法家思想與我國(guó)當(dāng)前的社會(huì)主義法制建設(shè)有許多地方不謀而合,我們應(yīng)該趨利避害,利用其中的若干啟示,汲取和借鑒其中的精華部分為社會(huì)主義法制建設(shè)服務(wù),充分利用古人的聰明才智,融古貫今,達(dá)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以往學(xué)者對(duì)儒家法律思想的研究,多依據(jù)傳世儒家文獻(xiàn),筆者在研讀戰(zhàn)國(guó)竹書中,發(fā)現(xiàn)上博竹書及郭店楚簡(jiǎn)中有幾條涉及法律的簡(jiǎn)文,為深入認(rèn)識(shí)儒家的倫理法思想提供了新資料,具有重要意義。本文擬在對(duì)這些簡(jiǎn)文進(jìn)行疏解的基礎(chǔ)上,重點(diǎn)對(duì)其所反映的儒家法思想作一論析,希冀對(duì)古代法律思想史研究有所裨益。
一、斷刑以哀與仁愛司法
上博簡(jiǎn)(五)《三德》云:“(若?)欲殺人,不飲不食。秉之不固,施之不威。至(致)型(刑)以哀,增去以謀。”①簡(jiǎn)文“殺人”②,當(dāng)指刑殺,古書中例證較多,如《呂氏春秋•仲秋紀(jì)》:“斬殺必當(dāng)。”高誘注:“軍刑斬,獄刑殺。”斬指軍刑,殺指刑獄之殺。《周禮•秋官•司刑》:“殺罪五百。”鄭玄注:“殺,死刑也。”《尚書•大禹謨》:“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jīng)。”此殺指刑殺。“至型”讀作“致刑”①。傳世文獻(xiàn)亦有“致刑”之詞,如《周易•豐卦》:“君子以折獄致刑。”孔疏云:“致用刑罰。”《尚書•多士》:“將天明威,致王罰。”屈萬(wàn)里注:“致,猶言推行。”②可見“致”有施加、施行、推行之意。“致刑以哀”,指在施用刑罰時(shí)要具有哀矜憐憫之心。上博簡(jiǎn)《天子建州》云:“斷刑則以哀。”③即要求司法人員以哀憐之心來斷刑,與“至刑以哀”意思相近。《尚書•呂刑》:“哀敬折獄。”曾運(yùn)乾《尚書正讀》云:“哀敬,敬當(dāng)為矜,憐也。言以哀矜之心折獄。”④《尚書大傳》引孔子曰:“聽獄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由此可見,哀戚斷刑觀念至少在《呂刑》時(shí)代即已產(chǎn)生。“秉”有“秉持”、“執(zhí)”等義。“秉之”指秉持刑法條文(荀子謂之“法數(shù)”,即司法條文等法律規(guī)定)。“施”指“施法”,即具體的司法實(shí)踐。“威”為威嚴(yán)之義,不威即無威嚴(yán),不能讓百姓畏刑。意即若秉持法律條文不嚴(yán),施行刑罰時(shí)則不具有威嚴(yán)。“謀”,謀略、計(jì)謀。儒家主張折獄決訟要公平,但并不能僅依法律條文來折獄,而是要求司法者具有“增去以謀”的能力。這種看似矛盾的思想,其理論支撐乃是儒家的“經(jīng)權(quán)”之道⑤。就司法實(shí)踐而言,所謂“經(jīng)”便是嚴(yán)格執(zhí)法,即“秉之不固,施之不威”;所謂“權(quán)”則是兼顧人情等法律外的因素,或增刑,或減刑,即“增去以謀”。據(jù)上考證,上引《三德》簡(jiǎn)文內(nèi)容具有整體連貫性,即均是論折獄致刑之事。關(guān)于“不飲不食”,范常喜認(rèn)為它與文獻(xiàn)中的“不飲酒”、“不食肉”相近似,當(dāng)指君王或從政者因嗜好殺人而內(nèi)心罪己的懺悔方式⑥。林文華則認(rèn)為“不飲不食”并非罪己,而是為了保持嚴(yán)肅莊重心態(tài)的緣故,在執(zhí)行刑罰殺人之前,宜保持嚴(yán)肅莊重的態(tài)度,不可從事飲酒食肉等作樂之事,以免影響用刑時(shí)的心情⑦。我們認(rèn)為,范、常二說均未切中肯綮,簡(jiǎn)文的關(guān)鍵是刑殺為何不飲酒不食肉,這須從先秦時(shí)期與刑殺相關(guān)古禮的角度來分析,方能深入理解簡(jiǎn)文的內(nèi)涵。刑殺在先秦時(shí)期屬于“大故”,《周禮•天官•膳夫》云:“邦有大故則不舉。”鄭玄注云:“大故,刑殺也。”刑殺在先秦即視作不祥兇事⑧。例如上博簡(jiǎn)(五)《季庚子問于孔子》云:“好刑則不祥,好殺則作亂。”⑨明代邱浚稱“刑乃不祥之器”,無疑代表了古代儒家知識(shí)分子的普遍看法瑏瑠。由于殺人之極刑屬于不祥兇事,加之死者不可復(fù)生,刑殺給死者及其家族帶來莫大恥辱,因此從西周到春秋,一直存在這樣一種司法傳統(tǒng),即國(guó)中出現(xiàn)刑殺時(shí),統(tǒng)治者應(yīng)在日常飲食方面加以節(jié)制①,以體現(xiàn)其“視民如傷”的仁愛之心與恤民之情。此禮在傳世文獻(xiàn)中多有記載,如《左傳•襄公二十六年》記載:“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所謂“不舉”,據(jù)《周禮•天官•膳夫》“王日一舉”鄭玄注“殺牲盛饌曰舉”,可知不舉即不殺牲,亦即不食肉。《國(guó)語(yǔ)•周語(yǔ)上》、《左傳•莊公二十年》均有“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的記載,行戮指刑殺,即司寇執(zhí)行刑殺時(shí),則國(guó)君不食肉。《禮記•文王世子》記載國(guó)君公族中有被執(zhí)行死刑的,則“公素服不舉”,亦遵守“不舉”之禮。后世文獻(xiàn)也有刑殺時(shí)統(tǒng)治者不食肉之說,如《后漢書•蔡邕傳》云:“君子斷刑,尚或?yàn)橹慌e。”晉代傅玄《傅子•法刑》:“司寇行刑,君為之不舉樂,哀矜之心至也。”需要進(jìn)一步探討的是簡(jiǎn)文“致刑以哀”與刑殺“不飲不食”主張背后的思想觀念。我們認(rèn)為,這與儒家對(duì)禮與刑兩種治國(guó)手段的深入認(rèn)識(shí)密切相關(guān),它體現(xiàn)出儒家以仁愛精神指導(dǎo)斷刑致刑的法律思想。
儒家主張治國(guó)應(yīng)將刑法與禮制相結(jié)合,如《禮記•樂記》云:“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將禮與刑均視作治國(guó)之道,是使民心向善的工具。郭店簡(jiǎn)《六德》篇亦提出“作禮樂,制刑法,教此民爾,使之有向也”②,認(rèn)為禮樂、刑法具有教化民眾、引導(dǎo)百姓具有正確的道德價(jià)值觀的功能。以“禮樂”、“刑法”為教民向善的治國(guó)之道,這是先秦儒家的一貫主張,問題是如何處理禮、刑這兩種治國(guó)手段在治國(guó)中的先后主次關(guān)系。儒家繼承了西周以來的德政傳統(tǒng),倡導(dǎo)仁政,提出了“仁者愛人”、“泛愛眾”、“為政以德”等主張,要求統(tǒng)治者愛民、富民、教民。在治國(guó)方略上,他們主張?jiān)诟幻窕A(chǔ)上,通過禮樂對(duì)百姓實(shí)行溫和的教化,使百姓“絕惡于未萌,而起敬于微眇”,“日徙善遠(yuǎn)罪而不知”(《大戴禮記•禮察》),從而實(shí)現(xiàn)國(guó)家的長(zhǎng)治久安。孔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yǔ)•為政》)。相較而言,禮樂教化使人知羞恥而無奸邪之心,使人真心向善,加強(qiáng)道德自律,不僅有預(yù)防犯罪的作用,而且可以得到百姓的擁護(hù),從而達(dá)到“無訟”和“勝殘去殺”的目的。而刑罰只是消極地禁止人為惡,以法制的威嚴(yán)使人不敢為惡,卻不能引人向善③。因此,儒家主張治國(guó)為政應(yīng)以禮樂教化、導(dǎo)民興德為先務(wù)。如郭店簡(jiǎn)《尊德義》云:“是以為政者教導(dǎo)之取先。教以禮,則民果以勁;教以樂,則民淑德清壯。……先之以德,則民進(jìn)善焉。”④孟子主張治國(guó)之道首先在于富民,百姓有恒產(chǎn)才會(huì)有恒心,然后再推行教化;如果排斥富民、教民之道而純粹以刑罰懲治百姓,就是“殃民”之舉(《孟子•告子下》)。基于這種認(rèn)識(shí),儒家強(qiáng)烈批評(píng)不教而誅無異于設(shè)坎陷坑害百姓,是典型的虐政。如《大戴禮記•盛德》說:“刑罰之所從生有源,不務(wù)塞其源而務(wù)刑殺之,是為民設(shè)陷以賊之也。”《論語(yǔ)•堯曰》記載孔子說:“不教而殺謂之虐。”只有在禮樂教化達(dá)不到目的的情況下,對(duì)那些不聽教化的冥頑之人方可施加刑罰,刑乃德治失效的情況下不得已而采用的補(bǔ)救措施。
儒家主張推行教化,關(guān)鍵在于為政者能夠以身作則。執(zhí)政者做好表率作用,則天下之人靡然向善歸德,國(guó)家大定。如《孟子•離婁上》云:“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guó)定矣。”郭店簡(jiǎn)《成之聞之》云:“古之用民者,求之于己為恒。行不信則命不從,信不著則言不樂。民不從上之命,不信其言,而能含德者,未之有也。故君子之立民也,身服善以先之,敬慎以寸(守)之,其所在者內(nèi)矣。”①執(zhí)政者能否取信于民,百姓是否聽從上命,關(guān)鍵在于執(zhí)政者能否“身服善以先之”。因此,儒家主張教化之道,治民者必須“求己”、“反本”,“以身服善”。由于禮樂教化之本在于治民者能否以身作則,做好表率作用,儒家認(rèn)為若百姓觸犯刑律,統(tǒng)治者應(yīng)負(fù)主要責(zé)任。《荀子•宥坐》所載孔子的一段話很有代表性:“嗚呼!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郭店簡(jiǎn)《成之聞之》亦將刑殺之訟歸于人君德行之失:“戰(zhàn)與刑人,君子之墜德也”,認(rèn)為“君子之于教也,其導(dǎo)民也不浸,則其淳也弗深矣。是故亡乎其身而存乎其詞,雖厚其命,民弗從之矣。是故威服刑罰之屢行也,由上之弗身也”②。總之,在先秦儒家思想中,對(duì)百姓犯罪的原因給予了較大的同情與理解,并將之歸結(jié)于上層執(zhí)政者的政教之失。由于百姓遭致刑罰的根源乃在于社會(huì)上層,而非百姓之過,故儒家將仁德精神注入了司法實(shí)踐,提倡仁者司法,“惟良折獄”(《尚書•呂刑》),并積極倡導(dǎo)恤刑,要求司法者應(yīng)有惻隱之心,矜憐觸犯法律的百姓③。《論語(yǔ)•子張》記載孟氏使陽(yáng)膚為士師,請(qǐng)教于曾子。曾子說:“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對(duì)于犯法百姓,司法者要體諒其犯罪的原因而哀矜之,不要因得案情之真而自喜其能。基于仁道思想,孟子主張治民者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孟子•公孫丑上》),應(yīng)以“常求其生”之心謹(jǐn)慎斷刑,并提出“以生道殺民”(《孟子•盡心上》)的主張,即司法者應(yīng)內(nèi)懷憐憫之心來聽獄斷訟,以“求其生”之道來審慎審理,能不殺的盡量不殺。這也是儒家“恕道”的換位思考,反映了儒家對(duì)犯罪根本原因的認(rèn)識(shí),體現(xiàn)了儒家的忠恕之仁。“哀矜勿喜”、“斷刑以哀”也是提醒司法者要慎刑,“義刑義殺”(《尚書•康誥》),確保折獄持平、不枉不縱、無所偏頗,它與孟子“生道殺民”的主張?jiān)诰裆鲜窍嗤ǖ摹?/p>
二、融情于法、情法相濟(jì)
儒家法律思想是一種倫理法。倫理法的重要特征是要求司法者在司法實(shí)踐中兼顧情理,以符合刑罰的“中刑”原則。楚簡(jiǎn)亦有類似論述,并從治國(guó)的高度主張情法協(xié)調(diào),從而達(dá)到國(guó)家大治。上博簡(jiǎn)《天子建州》論述斷刑原則云:“刑,屯(純)用青(情),邦喪;屯(純)用勿(物),邦喪;必中青(情)以羅于勿(物),幾(僟)殺而邦正。”④其中之“中青羅于物”,簡(jiǎn)文整理者認(rèn)為:“中青讀作中情,中訓(xùn)為正,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劉洪濤認(rèn)為“羅”讀為“麗”,訓(xùn)為“附”①。兩說解釋合理,可從。先秦文獻(xiàn)中,“情”有情實(shí)、誠(chéng)實(shí)盡心、感情、等多種含義,學(xué)者已有很多論述可參②,茲不具論。簡(jiǎn)文之“情”,具體到儒家的法律思想層面,其核心應(yīng)是包括“親親也,尊尊也,長(zhǎng)長(zhǎng)也,男女有別”、父慈子孝、君仁臣忠、長(zhǎng)惠幼順等親親、尊尊人倫道德意義上的情理,以及上文所論述的斷刑中司法者的惻隱不忍之心、仁愛之情等內(nèi)容③。“中”是中國(guó)古代哲學(xué)中的一個(gè)重要范疇,有適當(dāng)、適度、公平、不輕不重、不枉不縱、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等內(nèi)涵。簡(jiǎn)文“中情”,指要切中人情,乃是對(duì)情的適度運(yùn)用,反對(duì)極端的“純用情”。“物”,孫詒讓《周禮正義》:“物,猶法也,不物謂不如常法。”王引之《經(jīng)義述聞•通說上•物》也將“物”訓(xùn)作法:“物訓(xùn)為類,故又有法則之義。《大雅•烝民》篇: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周語(yǔ)》:昭明物則以訓(xùn)之。又曰: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則非仁也。物也,則也,皆法也。”④據(jù)孫、王之說,何有祖先生認(rèn)為簡(jiǎn)文“物”或可訓(xùn)作法,在簡(jiǎn)文中指具體的法律條文⑤。此說合理可從。綜上考證及學(xué)者研究,簡(jiǎn)文大意是指,斷刑時(shí)必須兼顧“情”和“法”(物),既不可純粹根據(jù)人情以斷,也不可僅僅拘泥法律條文,偏任任何一方則會(huì)導(dǎo)致國(guó)家滅亡;而應(yīng)當(dāng)在斷獄時(shí)“中情”且依據(jù)法律條文,要明察案情之實(shí),這樣國(guó)家才會(huì)安定。
司法公正是儒家法律思想的重要價(jià)值追求,但是如何實(shí)現(xiàn)司法的公正,儒家認(rèn)為應(yīng)堅(jiān)持情、法結(jié)合的原則,謹(jǐn)慎地?cái)嘈獭男塘P的實(shí)踐看,先秦有墨、劓、刖、宮、大辟等“五刑”,重則砍首,輕則傷人身體毀人容貌。而刑罰一旦施用,則對(duì)人的身體產(chǎn)生傷害難以更改。儒家對(duì)此有清醒的認(rèn)識(shí),《禮記•王制》說:“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郭店簡(jiǎn)《尊德義》云:“賞與刑,禍福之基也,或前之者矣。爵位,所以信其然也。征侵,所以攻[也]。刑[罰],所以與也。殺戮,所以除怨也。不由其道,不行。”⑥刑罰不遵守其道,則會(huì)產(chǎn)生嚴(yán)重的惡果,故而在司法實(shí)踐中要慎刑,尤其是對(duì)刑殺案件更要慎之又慎,要求斷刑者“悉聽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禮記•王制》)。慎刑的司法實(shí)踐原則,也要求在折獄時(shí)不要僅依據(jù)法律條文,而且應(yīng)全面考慮案情所涉的“情”、“理”,以求中正合宜。《禮記•王制》對(duì)慎刑規(guī)則與程式有詳細(xì)的論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quán)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cè)淺深之量以別之。”即凡斷刑,要權(quán)衡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等人倫道德情理,以及犯罪者罪行的嚴(yán)重程度,謹(jǐn)慎測(cè)度罪人的動(dòng)機(jī)善惡,以區(qū)別量刑的輕重。這些措施,其目的即為了保證刑罰實(shí)施的精詳審慎,要求斷刑必須兼顧人情與法,只有情法兩盡,才能做到斷刑明察端平,達(dá)到司法的公平。這種斷刑原則,對(duì)于防止出現(xiàn)濫刑、重刑具有積極意義。儒家追求中庸之道,體現(xiàn)在司法實(shí)踐上即追求“中刑”的境界,要求刑罰適中。簡(jiǎn)文提出將法律條文與情理結(jié)合起來定罪量刑的要求,即體現(xiàn)出儒家這一“刑罰尚中”的中刑思想,也是對(duì)西周以來“中刑”原則的繼承與發(fā)展①。從《天子建州》簡(jiǎn)文看,儒家將“情”置于司法實(shí)踐中的重要位置,認(rèn)為如果司法中純據(jù)法數(shù),則國(guó)家就會(huì)滅亡。因此,斷刑必須兼顧人情,“原情斷案”、“以情斷獄”,要做到“情法兩平”,將情限制在適中的程度,從而達(dá)到情法之間的平衡。但為了防止因私情而有害于公法,儒家又作了適度的調(diào)整,要求斷刑需“中情”而又據(jù)法,其原則是通情而不曲法,以維持法律的普遍有效性及權(quán)威性,否則,如《三德》簡(jiǎn)文所說:“秉之不固,施之不威”,則必然導(dǎo)致司法的不公平,削弱法律的威嚴(yán)。從這一角度分析,簡(jiǎn)文之“情”并非私情。另從文獻(xiàn)來看,儒家非常重視維護(hù)司法的威嚴(yán),提倡“治國(guó)制刑,不隱于親”(《左傳•昭公十四年》)。《禮記•文王世子》云:“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shù)也,所以體百姓也。”孫希旦《禮記集解》釋曰:“術(shù),法也。體百姓者,言與百姓為一體,而不可以有所私也。”②即公族犯法當(dāng)與百姓一視同仁,不能徇私情而縱放之。刑罰作為“禁邪”之具,若施行不當(dāng),則危害嚴(yán)重,因此必須嚴(yán)格執(zhí)法。故《禮記•王制》強(qiáng)調(diào)要“嚴(yán)斷刑”,“申嚴(yán)百刑,斬殺必當(dāng),毋或枉橈”。《禮記•緇衣》提出“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意即治民者不能以偏私的心態(tài)與行為來褻瀆刑罰、輕賞爵位。據(jù)上引述,可見秉公執(zhí)法是儒家的一貫主張。因此,儒家主張司法實(shí)踐中“執(zhí)權(quán)而守中”,斷刑以情,這絕不是主張以私情害公義或屈法伸情。簡(jiǎn)文要求“中情而麗于法”,目的亦在于消除情、法之間的沖突對(duì)立,除了防止出現(xiàn)人情對(duì)司法實(shí)踐的負(fù)面消極作用之外,更重要的是弱化刑法的剛性與機(jī)械性、冷酷性。儒家認(rèn)為,法治之下的為政者純粹以刑罰威逼百姓,缺乏心靈的溝通與情感的交流,如此造成上下之間離心離德,毫無親和力可言,往往會(huì)使百姓積怨③,以致于威脅到統(tǒng)治者的政權(quán)。在儒家法律思想中,純粹依賴刑罰本身并不能達(dá)到以刑止刑的目的,而刑罰的最終目的也并不在于懲戒,而是“以仁輔化”,即輔助教化(“弼教”),提高百姓的道德水平。《尚書•大禹謨》云:“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xié)于中。”呂思勉先生解釋說:“古代的用法,其觀念有與后世大異的,那便是古代的‘明刑’,乃所以‘弼教’。”④儒家主張刑罰與禮樂教化的目的是一致的,要充分發(fā)揮刑罰本身的教化功能,并藉此達(dá)到以刑去刑、以殺去殺的目的。而如果僅拘泥于法律條文,司法實(shí)踐中不顧及倫理人情,無疑會(huì)對(duì)社會(huì)價(jià)值觀、道德觀以及社會(huì)教化造成傷害。在司法實(shí)踐中融情于法,可使冷酷的機(jī)械性的刑罰呈現(xiàn)出些許溫彩,沖淡法的僵硬與冷酷的外貌⑤,在一定程度上可緩解刑罰造成的社會(huì)緊張,彌補(bǔ)法律的不足,維護(hù)社會(huì)的親和力,更有益于社會(huì)教化。總之,《天子建州》簡(jiǎn)文表明,儒家追求司法實(shí)踐中的“中刑”,要求司法者應(yīng)根據(jù)法律條文并兼顧情理,權(quán)衡處之,達(dá)到一種“中”的境界,從而確保司法公正。
三、儒法兩家法律思想之分歧
以上對(duì)簡(jiǎn)文思想內(nèi)涵的解讀,為思考儒法兩家法律思想的異同提供了一個(gè)有效的視角。從簡(jiǎn)文提供的時(shí)代背景分析,儒家斷刑“中情而麗于法”、“致刑以哀,增去以謀”等主張的提出,無疑乃是對(duì)法家法律思想的批判,體現(xiàn)出儒法兩家法律思想上的差異所在。儒法兩家法律思想的爭(zhēng)論,首先是關(guān)于仁義道德在司法實(shí)踐中的地位和作用問題。如上所論,儒家主張以仁義之道司法,司法者“斷刑以哀”,在司法實(shí)踐中滲透仁愛之情,這是儒家法律思想的重要特征。而法家根本否認(rèn)仁義道德的價(jià)值,認(rèn)為儒家的“仁政”根本不可能建立一個(gè)秩序井然的社會(huì),忠孝仁愛等倫理觀念并不能止亂,無益于治道。《商君書•畫策》提出:“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義者能愛于人,而不能使人愛。是以知仁義之不足以治天下也。”韓非從人性角度指出仁義之道根本無益于社會(huì)治理,他篤信人性本惡,無向善之可能,父子之間的關(guān)系也不過是利益關(guān)系,譬如父母“產(chǎn)男則相賀,產(chǎn)女則殺之”(《韓非子•六反》),因?yàn)閮鹤颖扰畠焊欣蓤D。由此,作為儒家政治思想出發(fā)點(diǎn)的家庭親情被徹底否定。儒家從親親之情推導(dǎo)出的以仁愛治理天下的主張,韓非更視之為荒謬透頂,極盡揶揄嘲諷、批判之能事,《韓非子•顯學(xué)》說:“母不能以愛持家,君安能以愛持國(guó)?”他明確宣稱:“故有道之主,遠(yuǎn)仁義,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譽(yù)廣而名威,民治而國(guó)安,知用民之法也”(《韓非子•說疑》)。因此,法家堅(jiān)決反對(duì)司法實(shí)踐中羼入仁義道德,對(duì)儒家“斷刑以哀”、“不飲不食”體現(xiàn)出的司法矜恤主義,法家更是強(qiáng)烈反對(duì),《韓非子•五蠹》有言:“今儒、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則視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為之不舉樂;聞死刑之報(bào),君為流涕。’此所舉先王也。……且夫以法行刑,而君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為治也。夫垂泣不欲形者,仁也;然而不可不行者,法也。先王勝其法,不聽其泣,則仁之不可以為治亦明矣。”韓非認(rèn)為,君主為受刑者不舉不作樂,泫然流淚,這不過是用來表現(xiàn)仁愛罷了,但并非治國(guó)之道。儒家將仁愛融入司法的另一個(gè)表現(xiàn),是其赦免小罪的矜恤主義司法主張,這也體現(xiàn)了儒家為政以寬、惠政仁政的政治思想。這種思想在儒家文獻(xiàn)中多有體現(xiàn),如《論語(yǔ)•子路》記載仲弓問政,孔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周易•解卦》:“君子以赦過宥罪。”《大戴禮記•子張問入官》:“民有小罪,必以其善,以赦其過,如死使之生,是以上下親而不離。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輔化;如有死罪,其使之生,則善也。”儒家認(rèn)為赦免小過,則刑罰不會(huì)被濫用,君民上下之間會(huì)親和而不相互背離。郭店簡(jiǎn)《五行》又將赦免小罪視作合于天道與人道,簡(jiǎn)文云:“不簡(jiǎn),不行。不匿,不察于道。有大罪而大誅之,簡(jiǎn)也。有小罪而赦之,匿也。有大罪而弗大誅也,不行也。有小罪而弗赦也,不察于道也。……簡(jiǎn),義之方也。匿,仁之方也。剛,義之方。柔,仁之方也。”①簡(jiǎn)是從實(shí)情出發(fā),遵循義的原則;匿是“有小罪而赦之”,是小的具體原則。前者是義,后者是仁;前者是剛,后者是柔。能簡(jiǎn)能匿,意指既能掌握大問題上的剛性原則,又具有在小問題上的權(quán)變能力。簡(jiǎn)文主旨是說,斷獄需剛?cè)嵯酀?jì),經(jīng)權(quán)兼顧,如此則符合仁義之道,方能中刑。
【關(guān)鍵詞】秦王朝;西漢王朝;法律制度;律令
一、秦代的法律制度的全面建立
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guó)后,以秦律為基礎(chǔ),參照六國(guó)法律,制定了通行全境的法律制度。從睡虎地出土的竹簡(jiǎn)可以看出,秦代法律大體有四種形式:(1)法律條文。其種類有:《田律》、《廄苑律》、《倉(cāng)律》、《金布律》、《軍爵律》、《置吏律》、《除吏律》等近三十種,包括政治、經(jīng)濟(jì)、軍事等各個(gè)方面。這些法律是由國(guó)家統(tǒng)一頒布的,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成文法。(2)對(duì)法律條文的解釋。統(tǒng)一之前,秦國(guó)行政機(jī)構(gòu)已設(shè)立專管法律的官吏,負(fù)責(zé)向其他官吏和人民咨詢法律,并將咨詢問答的內(nèi)容寫在一尺六寸長(zhǎng)的“符”上。符的左片交給咨詢者,右片放在官府封存?zhèn)洳椤#?)地方政權(quán)的文告。秦政府規(guī)定,郡一級(jí)政權(quán)可以依據(jù)朝廷法令制定本地區(qū)相應(yīng)的法令和文件,作為國(guó)家法令的一種補(bǔ)充。(4)有關(guān)判決程序的規(guī)定與證明。這是由朝廷統(tǒng)一的類似后來行政法和訴訟法的有關(guān)法令。
秦王朝的法律具有以下三個(gè)特點(diǎn):
第一,鮮明的階級(jí)性,維護(hù)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專制制度。秦律把商鞅變法以來的土地私有制用法律的形式確定下來,凡破壞或侵犯土地私有制和私有財(cái)產(chǎn)者,要以“盜賊”論處。秦律還規(guī)定:“受田”之民,要按“受田之?dāng)?shù)”征收賦稅,強(qiáng)迫農(nóng)民交納田賦。還要按照規(guī)定服徭役。不能按期繳納稅賦或服徭役的,要受到嚴(yán)厲的懲罰。
第二,法網(wǎng)嚴(yán)密,條目繁雜。秦律幾乎對(duì)人民生活的一舉一動(dòng)均作出明文規(guī)定,進(jìn)行嚴(yán)格限制,甚至治罪。“步過六尺者,有罰”,“敢有挾書者,族”,“誹謗者族”,“有敢偶語(yǔ)者,棄市”。甚至連穿鞋都作規(guī)定,致使百姓“毋敢履錦履”。這些無端的限制和懲治,形成“赭者塞路,囹圄成市”。 秦統(tǒng)治者認(rèn)為只有用重刑才能杜絕犯罪。
第三,堅(jiān)持“緣法而治” 的傳統(tǒng)。法令一經(jīng)公布,包括國(guó)君在內(nèi),任何人不得更改。《韓非子》中有記載秦昭王不因百姓殺牲為自己生病祈禱而循私情的故事。國(guó)君帶頭執(zhí)法,故“秦民皆趨令”,秦始皇繼承了祖宗的傳統(tǒng),堅(jiān)持“緣法而治”。二世時(shí)期用更加嚴(yán)酷的刑法,帶來的后果是秦王朝的迅速滅亡。
二、西漢初期對(duì)秦代法律的繼承
劉邦入關(guān)中時(shí)曾“約法三章”,西漢建立以后,為適應(yīng)新形勢(shì)的需要,丞相蕭何參考秦代法律,制定了《九章律》,包括“盜、賊、囚、捕、雜、具、興、廄、戶”律。此后的統(tǒng)治者不斷地對(duì)《九章律》中沿襲下來的秦的苛法加以汰除,如高帝時(shí)蕭何“除參夷,連坐之罪”,即廢除族刑和連坐之法。惠帝四年(前191年)又“除挾書律”。高后元年(前187年)再次重申“除三族罪、妖言令”。文帝元年(前179年)“盡除收帑相坐律令”。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下令“除肉刑”,將黥、劓、刖左右趾等肉刑分別改為笞三百、五百。景帝元年(前156年)又將笞五百改為笞三百,笞三百改為笞二百。之后又將笞三百為二百,笞二百為一百,同時(shí)還規(guī)定,“笞長(zhǎng)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jié)。當(dāng)笞者笞臀,毋得更人”。由于漢初的法制“禁罔疏闊”,所以在惠帝和呂后時(shí)期“刑罰用稀”,至文帝時(shí),更是“刑罰大省,至于斷獄四百”。雖然漢初“約法省禁”的記載與實(shí)際執(zhí)行的情況有一定距離,但與秦的嚴(yán)刑苛法相比,畢竟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刑罰,這對(duì)于穩(wěn)定社會(huì)秩序起到了促進(jìn)作用。
三、漢武帝時(shí)期以后法律制度的完備和發(fā)展
封建法制的強(qiáng)化和完善西漢建立之初,基于“無為而治”的統(tǒng)治思想,在法律上實(shí)行“約法省禁”的政策。隨著經(jīng)濟(jì)的恢復(fù)和發(fā)展,到漢武帝時(shí),客觀形勢(shì)要求統(tǒng)治者必須進(jìn)一步強(qiáng)化和完善封建法制,以加強(qiáng)專制主義中央集權(quán)。在這種情況下,漢武帝時(shí)期進(jìn)行了大規(guī)模的修改和制定法律的工作。
武帝一改文景時(shí)期的寬緩刑法,務(wù)求嚴(yán)刑峻法。據(jù)史書記載,在張湯和趙禹二人的主修之下,西漢的法律“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wàn)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于幾閣,典者不能遍睹”。
西漢中后期的法律制度,大致包括四方面形式:一是律。律是漢代法律的主要形式,這是一種比較穩(wěn)定的法律形式,晉朝杜預(yù)在《律序》中說:“律以正罪名”。除繼承漢初《九章律》的內(nèi)容以外,還制定了《越宮律》、《朝律》、《上計(jì)律》、《左官律》、《尚方律》等等。另外,相坐法、沉命法等也屬于“律”的范疇。二是令。董仲舒在其《春秋繁露》中竭力宣揚(yáng)天子受命于天,認(rèn)為“刑者君之所以罰也”。基于這種理論,皇帝的詔令便自然而然地成為封建法律的重要形式了。成文法如與在位皇帝的詔令發(fā)生抵觸,則以皇帝的詔令為準(zhǔn)。漢代“令”的數(shù)量相當(dāng)多,自高祖劉邦制定以來,至成帝時(shí)已達(dá)一百多萬(wàn)字。其內(nèi)容涉及到政治、經(jīng)濟(jì)、軍事、文化、社會(huì)生活等各個(gè)方面,成為當(dāng)時(shí)人們生活中的主要行為規(guī)范。三是科。科是規(guī)定犯罪與刑罰的另一種法律形式,多是關(guān)于人們?nèi)绾巫鳛榈囊?guī)范,類似于現(xiàn)代的行政法規(guī)和民事法規(guī)。“科”起源于漢初,“高祖受命,蕭何創(chuàng)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于致憂之義”;到漢武帝時(shí),“科”的內(nèi)容又有增加,“武帝軍役數(shù)興,豪杰犯禁,奸吏弄法,故重首匿之科”。四是比。又稱“決事比”,就是以典型案例作為判決的標(biāo)準(zhǔn)。高祖時(shí)即規(guī)定,凡廷尉不能決斷的案件,應(yīng)當(dāng)附上所應(yīng)比附的律令條文,上奏皇帝。至武帝時(shí),“死罪決事比萬(wàn)三千四百七十二事”。由于諸比之間互相矛盾,處罰也輕重不一,以至奸猾之吏借機(jī)徇私枉法。
除以上四種法律形式外,漢武帝時(shí)還出現(xiàn)一種特別的法律形式,就是“春秋決獄”。所謂“春秋決獄”,就是將《春秋》一書中的“微言大義”作為判斷案件的根據(jù)。這種決獄標(biāo)準(zhǔn)的出現(xiàn),是因?yàn)闈h武帝將儒學(xué)作為統(tǒng)治思想,而《春秋》正是儒家經(jīng)典的《五經(jīng)》之一。用《春秋》的精神和內(nèi)容作為審判的依據(jù),這就把儒家的經(jīng)典當(dāng)成了法律。其次,由于武帝時(shí)制定的法律條文相當(dāng)繁雜。而用《春秋》中表達(dá)得并不十分明確的觀念來斷獄,便可以拋開繁瑣的法律條文和客觀事實(shí),根據(jù)需要作出各種解釋。這樣,“春秋決獄”可以給統(tǒng)治者和執(zhí)法者帶來更大的方便,甚至可以不受律令的限制,自然便很快盛行起來。漢武帝曾要求他的兒子學(xué)好《公羊春秋》,以便將來作為處理國(guó)事的根據(jù)。皇帝如此提倡,各級(jí)官吏自然就積極奉行起來了。“春秋決獄”這種以儒家思想為審判依據(jù)的特殊的法律形式不但對(duì)兩漢法律產(chǎn)生了直接的影響,而且對(duì)以后兩千年的中國(guó)古代封建法制也有深遠(yuǎn)的影響。
【參考文獻(xiàn)】
[1]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59.
[2]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2.
[3]范曄.后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5.
[4]李.太平御覽[M].北京:中華書局,2011.
論文內(nèi)容摘要:從目前刑法的規(guī)定來看,主張遺棄罪非身份犯的身份犯否定說并不可取,遺棄罪應(yīng)當(dāng)屬于身份犯的一種,其主體應(yīng)當(dāng)是因婚姻家庭關(guān)系而負(fù)有扶養(yǎng)義務(wù)的人。
遺棄罪是指對(duì)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沒有獨(dú)立生活能力的人,負(fù)有扶養(yǎng)義務(wù)而拒絕扶養(yǎng),情節(jié)惡劣的行為。
我同刑法1997修訂之時(shí),在保持了遺棄罪條文表述不變的前提下將該罪名在分則中的位置進(jìn)行了改動(dòng),也正是因?yàn)檫@一“位移”而導(dǎo)致了理論界有關(guān)遺棄罪是否身份犯的討論,尤其是這種爭(zhēng)論在司法實(shí)踐中也有所體現(xiàn)。
我國(guó)舊《刑法》(指1979年《刑法》,下同)將遺棄罪規(guī)定在“妨害婚姻家庭罪”一章中,因此學(xué)界及實(shí)務(wù)界認(rèn)為遺棄罪只能發(fā)生在婚姻家庭內(nèi)部而毫無爭(zhēng)議地將遺棄罪作為身份犯的一種,在此前提下論說遺棄罪的相應(yīng)構(gòu)成:其客體是公民在家庭中接受扶養(yǎng)的權(quán)利,類似表述為“被害人在家庭中受扶養(yǎng)的權(quán)利義務(wù)關(guān)系”、“被害人在家庭中的平等權(quán)利”、“家庭成員之間互相扶養(yǎng)的權(quán)利義務(wù)關(guān)系”,等等。作為遺棄罪對(duì)象(或被害人)的“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沒有獨(dú)立生活能力的人”,顯然只能是家庭成員;法條圈定本罪主體為“負(fù)有扶養(yǎng)義務(wù)”的人,也就限于因婚姻家庭關(guān)系而負(fù)有扶養(yǎng)義務(wù)的人。這種關(guān)于遺棄罪構(gòu)成要件的理解以及該罪身份犯性質(zhì)的認(rèn)定在舊刑法時(shí)代幾乎沒有疑義。
在新刑法修訂過程中,由于舊刑法作為獨(dú)立章所規(guī)定的“妨害婚姻家庭罪”項(xiàng)下只有六個(gè)條文而略顯單薄,與其他章的規(guī)模不協(xié)調(diào),因此經(jīng)過學(xué)者的充分討論,立法機(jī)關(guān)最終決定將原來單設(shè)一章的“妨害婚姻家庭罪”歸并到刑法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權(quán)利、民主權(quán)利罪中。應(yīng)當(dāng)說這一歸并是比較合理的,充分考慮了刑法分則體系上的協(xié)調(diào)和科學(xué)。但是,正是這一位置上的變動(dòng)而引發(fā)了理論界及實(shí)務(wù)部門對(duì)遺棄罪屬于身份犯性質(zhì)的否定和犯罪構(gòu)成要件的重新詮釋:遺棄罪的主體與對(duì)象不需要是同一家庭成員。扶養(yǎng)義務(wù)不能僅根據(jù)婚姻法確定,而應(yīng)根據(jù)不作為義務(wù)來源的理論與實(shí)踐(如法律規(guī)定的義務(wù)、職務(wù)或業(yè)務(wù)要求履行的義務(wù)、法律行為導(dǎo)致的義務(wù)、先前行為導(dǎo)致的義務(wù)等)確定。基于同樣的理由,遺棄罪的對(duì)象也不限于家庭成員。筆者稱之為身份犯否定說。
贊同身份犯否定說學(xué)者所持有的理由歸納起來主要有三,筆者一一加以評(píng)說:
其一,對(duì)具體犯罪直接客體內(nèi)容的確定,離不開該罪所屬類罪的同類客體要件的內(nèi)容,具體犯罪的直接客體要件內(nèi)容不得超出同類客體的內(nèi)容,否則,《刑法》就不會(huì)將該罪規(guī)定在這一章中。遺棄罪既然被1997年《刑法》規(guī)定在侵犯人身權(quán)利、民主權(quán)利罪這一章中,說明遺棄罪的同類客體要件是公民的人身權(quán)利。在此前提下,遺棄罪直接客體要件的內(nèi)容不應(yīng)超出這一限制,否則,遺棄罪就不可能屬于侵害人身權(quán)利、民主權(quán)利罪這一章。申言之,遺棄罪是對(duì)公民人身權(quán)利的侵犯。遺棄罪直接客體要件是公民的生命、健康,而不能像以前那樣將遺棄罪理解為對(duì)婚姻家庭關(guān)系、對(duì)公民在家庭中受撫養(yǎng)權(quán)利的侵犯,因?yàn)榛橐黾彝リP(guān)系不屬于人身權(quán)利的范疇。
由于我國(guó)刑法中作為某一具體犯罪構(gòu)成必備要件之一的犯罪客體(法益)并沒有直接在法條中明示,一般都是通過法律條文對(duì)犯罪客觀要件的規(guī)定以及結(jié)合罪名所處章節(jié)之與類罪名相對(duì)應(yīng)的同類客體進(jìn)行判斷。因此,論者的推理過程是:遺棄罪被規(guī)定在侵犯公民人身權(quán)利、民主權(quán)利罪一章中,該章的同類客體是公民的人身權(quán)利和民主權(quán)利,公民的生命、健康權(quán)利屬于公民人身權(quán)利(同類客體)之一種而公民在家庭中接受扶養(yǎng)的權(quán)利則否,因此本著直接客體不能超越同類客體的原則得出遺棄罪的客體只能是公民的生命、健康權(quán)利這一結(jié)論。這里存在一個(gè)問題便是,作為侵犯公民人身權(quán)利、民主權(quán)利罪之同類客體的公民人身權(quán)利和民主權(quán)利如何理解?公民在家庭中接受扶養(yǎng)的權(quán)利是否包含其中呢?所謂犯罪的同類客體,是指某一類犯罪行為所共同侵害的我國(guó)刑法所保護(hù)的社會(huì)關(guān)系的某一部分或某一方面。劃分犯罪的同類客體,是根據(jù)犯罪行為侵害的刑法所保護(hù)的社會(huì)關(guān)系的不同進(jìn)行的分類。作為同一類客體的社會(huì)關(guān)系,往往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性質(zhì)。因此,犯罪的同類客體之范圍應(yīng)當(dāng)具有一定的宏觀性和抽象性,需要對(duì)若干具體犯罪所侵犯的直接客體進(jìn)行高度概括。作為刑法分則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權(quán)利、民主權(quán)利罪而言,所指稱的人身權(quán)利這一同類客體一般都認(rèn)為是指法律所規(guī)定的與公民的人身不可分離的權(quán)利,只有權(quán)利人本人享有,包括生命權(quán)、健康權(quán)、性的自己決定權(quán)、人身自由權(quán)、人格名譽(yù)權(quán)、婚姻家庭方面的權(quán)利,以及與人身直接有關(guān)的住宅不受侵犯權(quán)等。重在強(qiáng)調(diào)這類權(quán)利的人身屬性。因此作為遺棄罪保護(hù)客體的公民在家庭中接受扶養(yǎng)的權(quán)利屬于婚姻家庭方面權(quán)利的一種當(dāng)無可非議,同樣基于此一權(quán)利的人身屬性特征而將其作為人身權(quán)利之一種也屬情理之中。因此不存在直接客體超越同類客體的問題。
從反面也可以得出類似結(jié)論:1997年《刑法》將舊刑法“妨害婚姻、家庭罪”中的6個(gè)罪名歸并到侵犯公民人身權(quán)利、民主權(quán)利罪一章中,其中包括虐待罪、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等,那么是否意味著所有這些罪名侵犯的客體都應(yīng)當(dāng)理解為公民的生命、健康權(quán)利呢?顯然答案是否定的。因此這種單單以法條位置的變化推斷法益的變化,再以之對(duì)犯罪構(gòu)成特征進(jìn)行重新詮釋的做法并不可取。
其二,如果只將遺棄罪保護(hù)的法益確定為傳統(tǒng)觀點(diǎn)所認(rèn)為的被害人在家庭中的平等權(quán)利或者家庭成員之間互相扶養(yǎng)的權(quán)利義務(wù)關(guān)系,那么該罪的行為對(duì)象就可能被人為地縮小解釋為家庭成員中的下列人員:因年老、傷殘、疾病而喪失勞動(dòng)能力,因而沒有生活來源的人;雖有退休金等生活來源,但因年老、傷殘、疾病而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因年幼尚無獨(dú)立生活能力的人。但是,在實(shí)踐中被遺棄的對(duì)象并不只是這些人。將遺棄罪的成立限于親屬之間乃是古代宗法社會(huì)以來的傳統(tǒng),立法者一直認(rèn)為親屬之間不履行撫養(yǎng)義務(wù),就對(duì)倫理規(guī)則有所違反。近代以來,生產(chǎn)力發(fā)達(dá),事故頻發(fā),個(gè)人陷于危難境地、無法自救的可能性增強(qiáng)。因此,遺棄罪的適用范圍往往不再局限于具有扶養(yǎng)義務(wù)的親屬之間,遺棄罪的本質(zhì)也不僅僅是對(duì)義務(wù)之違反,而且也是對(duì)于生命法益構(gòu)成威脅的危險(xiǎn)犯。
這一否定理由主要是基于一種現(xiàn)實(shí)性的考慮,從司法實(shí)踐中發(fā)生的案例來看,非家庭成員間的遺棄以及不履行救助義務(wù)的遺棄行為確實(shí)存在且有多發(fā)趨勢(shì),這不得不引起我們的重視。但是這種呼喚刑罰懲治的現(xiàn)實(shí)需要也絕不能作為我們沖破罪刑法定原則而對(duì)法律條文進(jìn)行隨意解釋的理由。這里涉及到一個(gè)更深層次的問題,就是對(duì)于遺棄罪進(jìn)行解釋時(shí)的方法選擇問題。有學(xué)者站在客觀解釋論的立場(chǎng),認(rèn)為立法者表達(dá)立法意圖的惟一工具是文字,解釋者應(yīng)當(dāng)通過立法者所使用的文字的客觀含義來發(fā)現(xiàn)立法意圖,因此可以將遺棄罪解釋為包括非家庭成員間的遺棄行為。而有的學(xué)者認(rèn)為對(duì)此問題應(yīng)當(dāng)采取沿革解釋的立場(chǎng),即從舊刑法將遺棄罪作為妨害婚姻、家庭罪之一種,而1997年《刑法》則將法條原原本本的移植到侵犯公民人身權(quán)利,民主權(quán)利一章中,因此該法律規(guī)定的含義并沒有變動(dòng)。本文筆者并不反對(duì)客觀解釋論,認(rèn)為法律條文用語(yǔ)當(dāng)然都有其相應(yīng)的客觀含義存在。但是這種客觀解釋論所強(qiáng)調(diào)之客觀絕不應(yīng)當(dāng)是現(xiàn)實(shí)問題出現(xiàn)而法律并無相應(yīng)規(guī)制的情況下就要對(duì)法條進(jìn)行擴(kuò)張解釋,而應(yīng)當(dāng)是對(duì)法律條文相關(guān)用語(yǔ)之適當(dāng)解釋。回歸到遺棄罪的探討上來,實(shí)則是對(duì)法律條文所表述的“扶養(yǎng)義務(wù)”之解釋,因?yàn)檫z棄罪只能是負(fù)有扶養(yǎng)義務(wù)的人才能實(shí)施。而根據(jù)我國(guó)《婚姻法》等相關(guān)法律規(guī)定,我國(guó)法律上的扶養(yǎng)包括四種:夫妻間的扶養(yǎng)(《婚姻法》第20條)、父母子女間的扶養(yǎng)(《婚姻法》第21條)、祖孫間的扶養(yǎng)(《婚姻法》第28條)、兄弟姐妹間的扶養(yǎng)(《婚姻法》第29條)。這一理解應(yīng)當(dāng)作為我們認(rèn)定《刑法》中遺棄罪的“扶養(yǎng)”義務(wù)之法律根據(jù)。況且這里的扶養(yǎng)義務(wù)應(yīng)當(dāng)與扶助(救助)義務(wù)相區(qū)別,不履行救助義務(wù)同樣也存在一個(gè)遺棄問題,但這種遺棄與基于法律規(guī)定的扶養(yǎng)義務(wù)之遺棄畢竟不同,而不能做同義理解。
關(guān)鍵詞:效力性規(guī)定;悖法性;策源性;失補(bǔ)正性;當(dāng)罰性
中圖分類號(hào):D923.6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文章編號(hào):16723198(2010)01024902
1 問題的提出
《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合同法》第52條對(duì)有關(guān)合同無效情形進(jìn)行了列舉性說明,其中第(五)項(xiàng)規(guī)定,違反法律、行政法規(guī)的強(qiáng)制性規(guī)定的合同無效。對(duì)于“強(qiáng)制性規(guī)定”,《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合同法司法解釋(二)》(以下簡(jiǎn)稱《合同法解釋二》)把“強(qiáng)制性規(guī)定”的用語(yǔ)進(jìn)一步明確其是指“效力性強(qiáng)制性規(guī)定”。強(qiáng)制性法律規(guī)范原本進(jìn)一步包含“管理性規(guī)范”和“效力性規(guī)范”。《合同法解釋二》用這一限制性解釋,把管理性規(guī)定從強(qiáng)制性規(guī)定中剔除,在判定合同效力時(shí)“強(qiáng)制性規(guī)定”專指“效力性強(qiáng)制性規(guī)定”。這樣,科學(xué)地縮小了判定合同無效的依據(jù)范圍。避免了因把“強(qiáng)制性規(guī)定”同合同效力一律關(guān)聯(lián),疏于區(qū)分立法目的、過分干涉意思自治,造成對(duì)違反法律“強(qiáng)制性規(guī)定”的合同皆武斷做出無效處理局面的繼續(xù)出現(xiàn)。《合同法解釋二》完善了合同無效制度,援引違反法律、行政法規(guī)的“強(qiáng)制性規(guī)定”來判定合同無效,就需要進(jìn)一步確定“強(qiáng)制性規(guī)定”到底屬于“管理性”的規(guī)定(又稱“取締性”)還是“效力性”的規(guī)定。違反效力性強(qiáng)制性規(guī)定,合同確定無效。違反管理性強(qiáng)制性規(guī)定,合同效力一般不作無效處理。
2 對(duì)已有認(rèn)定方法的簡(jiǎn)述
準(zhǔn)確認(rèn)定強(qiáng)制性效力性規(guī)定,實(shí)施起來是個(gè)復(fù)雜的事情。強(qiáng)制性規(guī)定一般以三種情況出現(xiàn)。第一種情況:強(qiáng)制性規(guī)定本身直接規(guī)定了違法行為的效力。第二種情況:強(qiáng)制性規(guī)定本身沒有直接明確規(guī)定違法行為的效力,但引致或結(jié)合其他法律條文,其他法律條文明確規(guī)定了該違法行為效力。第三種情況:強(qiáng)制性規(guī)定本身沒有直接明確規(guī)定違法行為的效力,也沒有引致到其他具體的法律條文中,更沒有其他法律條文對(duì)其效力予以明確規(guī)定。
前兩種情況,法律有明確的效力規(guī)定,依規(guī)定確定即可。但是第三種情況由于沒有規(guī)定行為的效力,那么到底如何把效力性規(guī)定同管理性規(guī)定、指導(dǎo)性規(guī)定或取締性規(guī)定相區(qū)分就成了問題的關(guān)鍵所在。
對(duì)于強(qiáng)制性效力性規(guī)定的區(qū)分方法,王利明教授提出三分法:第一,法律、法規(guī)規(guī)定違反該規(guī)定,將導(dǎo)致合同無效或不成立的,為當(dāng)然的效力性規(guī)定;第二,法律、法規(guī)雖然沒有規(guī)定:違反其規(guī)定,將導(dǎo)致合同無效或不成立。但違反該規(guī)定若使合同繼續(xù)有效將損害國(guó)家利益和社會(huì)公共利益,這也屬于效力性規(guī)定;第三,法律、法規(guī)沒有規(guī)定:違反其規(guī)定,將導(dǎo)致合同無效或不成立,雖然違反該規(guī)定,但若使合同繼續(xù)有效并不損害國(guó)家利益和社會(huì)公共利益,而只是損害當(dāng)事人利益的,屬于取締性規(guī)定(管理性規(guī)定)。
以上規(guī)定,從正面歸納了什么是效力性強(qiáng)制性規(guī)定,簡(jiǎn)明、有序,有助于區(qū)分效力性強(qiáng)制性規(guī)定。但是,此分法還只是對(duì)《合同法》第五十二條規(guī)定的概括。法律明確規(guī)定無效的,合同當(dāng)然無效是應(yīng)有之義。《合同法》第五十二條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無效:(一)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訂立合同,損害國(guó)家利益;(四)損害社會(huì)公共利益;上述歸納的第二種情況正好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一項(xiàng)和第四項(xiàng)一致,但是如何認(rèn)定“國(guó)家利益”、“社會(huì)公共利益”至今缺乏明確的標(biāo)準(zhǔn),從而導(dǎo)致第二種情況同第三種情況還是無從準(zhǔn)確區(qū)分。 可見,上述論述有積極的意義,但依然沒有滿足到可以判斷所有強(qiáng)制性規(guī)范的程度。
還有學(xué)者認(rèn)為,可以從強(qiáng)制性規(guī)定所針對(duì)的對(duì)象來對(duì)效力性和取締性規(guī)定進(jìn)行分類。也共分三類。第一類禁止性規(guī)定禁止的是“某一類型的合同行為”,當(dāng)事人不得為該合同行為,因?yàn)閷?duì)于此類型的合同行為,只要發(fā)生就會(huì)損害國(guó)家利益或者社會(huì)公共利益。第二類禁止性規(guī)定禁止的是市場(chǎng)準(zhǔn)入的主體、時(shí)間和地點(diǎn)問題,它與合同行為無關(guān),相應(yīng)的合同行為本身依然為法律所允許。第三類禁止性規(guī)定禁止的是合同的履行行為,合同本身依然有效,不能履行所要承擔(dān)的是違約責(zé)任。這三類行為中,第一類為強(qiáng)制性效力性規(guī)定,后兩者為管理性規(guī)定。
這些歸納給出了以禁止對(duì)象為分類的思路,具有積極意義,但其不周延更加明顯,從而導(dǎo)致應(yīng)用性的欠缺。因?yàn)椤澳骋活愋偷暮贤袨椤蓖笆袌?chǎng)準(zhǔn)入的主體、時(shí)間和地點(diǎn)問題”沒有進(jìn)一步區(qū)分。沒有給怎樣“對(duì)號(hào)入座”一個(gè)可以判定的特征導(dǎo)向。如對(duì)保險(xiǎn)業(yè)、金融業(yè)的從業(yè)主體資格限制,違法從事保險(xiǎn)業(yè)或者吸儲(chǔ)的按照這種說法完全可以認(rèn)為是對(duì)“市場(chǎng)準(zhǔn)入的主體、時(shí)間和地點(diǎn)的限制問題”,這似乎是有效行為了。(因?yàn)?無法知曉這屬于某一類型的合同還是 “對(duì)市場(chǎng)準(zhǔn)入的主體、時(shí)間和地點(diǎn)的限制問題”。)但事實(shí)上為了保障特別重要的公共利益,為了維護(hù)金融秩序,此行為是應(yīng)認(rèn)定行為無效,顯然是效力性規(guī)定而不是管理性規(guī)定。
3 重構(gòu)效力性強(qiáng)制性規(guī)定的認(rèn)定方法
第一,從公法對(duì)私法的必要規(guī)制看效力性規(guī)范。
比如:公法若是大街馬路上偶爾出現(xiàn)的威武而安靜的交警,那么私法可看做大街上馬路上的車輛、行人。后者各行其道,輕松、自由歡快。前者,安靜地巡視著,保障道路的暢通和后者的安全。如果一個(gè)汽車發(fā)動(dòng)機(jī)不小心熄了火,一下子沒有啟動(dòng)起來。交警往往會(huì)過來幫助推車,讓發(fā)動(dòng)機(jī)發(fā)動(dòng),繼續(xù)前行,保持路面暢通。這是公對(duì)私的干涉,但是管理性的,就像合同法里的管理性規(guī)范,通過補(bǔ)正手段讓合同繼續(xù)履行。但是,如果一個(gè)汽車,占道逆行,撞壞了另一輛汽車。這時(shí),交警就可能要把該肇事汽車拖走,而不惜犧牲該汽車?yán)^續(xù)前行的權(quán)益。
交警動(dòng)用拖車等處罰措施,就像合同法的強(qiáng)制性效力性規(guī)范的動(dòng)用。而交警的勸導(dǎo)和幫助,則是管理性規(guī)范。如果交警過于頻繁地動(dòng)用處罰措施,不時(shí)地封路拖車;那么,將會(huì)造成很多車輛、行人無法順利達(dá)到目的地,車輛行人就沒有了自己自主的預(yù)期。相反,如果交警過于“無為”,任憑車輛橫沖直撞,那么道路也會(huì)是兇險(xiǎn)異常。交警的處罰和幫助兩種方式要有良好的平衡。所以交警在無礙交通秩序的前提下,要盡可能地少封路、攔車,從而讓車輛行人走得了、走得好。
同樣公法對(duì)私法的規(guī)范進(jìn)行規(guī)制就是通過強(qiáng)制性規(guī)范來進(jìn)行。依法律的強(qiáng)制性效力性規(guī)范宣告合同無效,是公法性權(quán)力對(duì)私法意思自治權(quán)利的徹底否定,打破了當(dāng)事人對(duì)自我財(cái)產(chǎn)的處分安排,使合同利益落空。為了保護(hù)公共利益,維護(hù)公平正當(dāng)?shù)纳鐣?huì)秩序,這是必要的手段,但又必須慎重使用,否則會(huì)造成背離立法目的,侵害弱小者利益,有損交易安全和資源的順暢配置。所以,把強(qiáng)制性規(guī)范進(jìn)一步自分為強(qiáng)制性管理性規(guī)范和效力性規(guī)范等就應(yīng)運(yùn)而生了。
第二,認(rèn)定強(qiáng)制性效力性規(guī)范的標(biāo)準(zhǔn)必須符合“悖法性、策源性、失補(bǔ)正性、當(dāng)罰性”四要素。
首先,如前所述強(qiáng)制性規(guī)定本身直接規(guī)定了違法行為的效力;強(qiáng)制性規(guī)定本身沒有直接明確規(guī)定違法行為的效力,但引致或結(jié)合其他法律條文,其他法律條文明確規(guī)定了該違法行為效力。皆屬于確定滿足以上四要素的效力性規(guī)范。
其次,對(duì)于觸犯合同無效的強(qiáng)制性效力性規(guī)定構(gòu)成四要素的理解。
一是“悖法性”。悖法性是指同法律、行政法規(guī)(不包括部門規(guī)章、地方性法規(guī))的具體條款或原則相違背。
如果違反的是部門規(guī)章或地方性法律,則不能直接以違反部門規(guī)章或地方性法規(guī)為依據(jù)來判斷合同無效。這時(shí)候,部門規(guī)章和地方性法規(guī)可以作為啟迪思路的參考。審查該部門規(guī)章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規(guī)的原則。如果符合法律、行政法規(guī)的原則。那么,很可能該行為也直接違反了法律、行政法規(guī)的原則。此時(shí)則可依違反法律、行政法規(guī)的原則為由判斷合同無效。如損害公共利益可為判斷合同無效的理由。如果部門規(guī)章、地方性法規(guī)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規(guī)的規(guī)定,也不符合部門規(guī)章、地方性法規(guī)的原則精神。如實(shí)行地方保護(hù)的法規(guī)。則雖然違反了部門規(guī)章或地方性法規(guī),可以直接以沒有法律、行政法規(guī)的依據(jù)為由,認(rèn)定合同有效。
二是策源性。策,中國(guó)古代趕馬用的棍子,一段有尖刺,能刺馬的身體,使它向前跑。也有謀劃,籌劃之意。如策應(yīng)。源,水流起頭的地方如河源,泉源,源遠(yuǎn)流長(zhǎng),飲水思源。所謂策源性在文中意指規(guī)范自始即對(duì)行為及結(jié)果持根本否定的態(tài)度。即史尚寬所說,效力規(guī)定著重違反行為之法律行為價(jià)值,以否認(rèn)其法律效力為目的;而取締規(guī)定(管理性規(guī)定)著重違反行為之事實(shí)行為價(jià)值,以禁止其行為為目的。
判斷是否具有策源性的方法,一是看規(guī)范側(cè)重的是管理行為還是目的。(或者管理行為的本身也包含目的行為。)不可容忍目的行為的,為具有策源性質(zhì)的規(guī)定。二是具有對(duì)國(guó)家利益和社會(huì)公共利益以及其他重大利益的直接觸及性。三是一般規(guī)定側(cè)重的是行為的內(nèi)容,對(duì)主體資格鮮有規(guī)定,除非該主體資格事涉特別保護(hù),并在合同關(guān)系中造成主要實(shí)質(zhì)要件的欠缺,直接造成內(nèi)容的不可容忍。
三是失補(bǔ)正性。從立法目的看,如果是為了實(shí)現(xiàn)管理的需要而設(shè)置,而不是為了側(cè)重內(nèi)容的本身,并且其本身結(jié)果的出現(xiàn)并非不可容忍,甚至結(jié)果本身還有促進(jìn)流轉(zhuǎn)的益處,則是管理性規(guī)定。這管理性規(guī)定具有事后的補(bǔ)正性。所謂失補(bǔ)正性是指行為本身及其結(jié)果自始受到嚴(yán)厲的否定性評(píng)價(jià),不得補(bǔ)正后有效。
四是當(dāng)罰性。所謂當(dāng)罰性是指:該規(guī)范所指的行為,必須處罰,否則其行為及造成的結(jié)果“繼續(xù)存在”會(huì)造成嚴(yán)重危害。如果禁止履行的已經(jīng)實(shí)際履行了,在不違反合同法五十二條一至四項(xiàng)的條件情況下,為不當(dāng)罰。比如,建成并實(shí)際驗(yàn)收合格的建筑物,無資質(zhì)的建筑承包人得按照合同主張權(quán)利。這時(shí),由于建筑承包人已經(jīng)按要求驗(yàn)收合格,并沒有因?yàn)槠渲黧w資格缺乏而給對(duì)方當(dāng)事人造成損失。至于其應(yīng)當(dāng)履行行政上的管理手續(xù),即要求申領(lǐng)相應(yīng)的資質(zhì)證書則是行政管理上的問題;雖然沒有相應(yīng)資質(zhì)證書,在合同履行的實(shí)質(zhì)要求都成就的情形下,卻還用沒有資質(zhì)證書為由去斷定合同無效,并按照合同無效來處理當(dāng)事人的權(quán)利義務(wù)就會(huì)構(gòu)成過度干涉當(dāng)事人意思自治并造成社會(huì)資源的浪費(fèi)。《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審理建設(shè)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建設(shè)工程施工合同無效,但建設(shè)工程經(jīng)竣工驗(yàn)收合格,承包人請(qǐng)求參照合同約定支付工程價(jià)款的,應(yīng)予支持。雖然字面上是把“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業(yè)資質(zhì)或者超越資質(zhì)等級(jí)”的情形下簽訂的合同認(rèn)定為無效,但處理方式依然參照合同有效。所以,對(duì)于“不應(yīng)當(dāng)罰”的情形,不可認(rèn)定為效力性強(qiáng)制性規(guī)定。因?yàn)?即使援用假定的效力性強(qiáng)制性規(guī)定,而判定“合同無效”,也無法按照“合同無效”的定性去不加修正地處理。
參考文獻(xiàn)
一、 以古代詩(shī)詞引入,先聲奪人,出其不意,旁征博引
思想品德課教學(xué)的導(dǎo)入方法多種多樣,以古代詩(shī)詞引入是常用的方法。但一些教師在引用古詩(shī)詞時(shí)往往是一帶而過或者喧賓奪主,因此把握引入的度就顯得非常重要,這里就概括為先聲奪人,出其不意,最終旁征博引。具體說來,就是在原本學(xué)生熟悉的思想品德課中出乎學(xué)生意料地引用古代詩(shī)詞,接著再進(jìn)行品德的滲透,學(xué)生在消除了對(duì)這門課的思維慣性后激發(fā)了求知的欲望,思維變得開闊。舉例說明:首先呈現(xiàn)唐代李白的《江夏別宋之悌》和《早發(fā)白帝城》這兩首詩(shī);然后再提出兩首詩(shī)都寫長(zhǎng)江但所表達(dá)的情感有什么不同的問題,學(xué)生就會(huì)回答出前者反映出作者流放時(shí)經(jīng)過長(zhǎng)江,心情低落,后者反映出作者流放歸來再次經(jīng)過長(zhǎng)江,赦免后興奮之情喜形于表;最后加以總結(jié)得出這些都是情緒的流露,并且指出前者的消極情緒和后者的積極情緒是可以相互轉(zhuǎn)換的。另外還可以從法律角度出發(fā),古代刑罰中有流放這種方式,那么就可以問學(xué)生當(dāng)代刑罰的相關(guān)知識(shí),然后再探究古今刑罰的區(qū)別。這樣的過程給學(xué)生留下的痕跡要深刻得多,思維跨度大,拓展層面廣,所起效果佳。
二、 以古代詩(shī)詞點(diǎn)綴,思想品德課教學(xué)可錦上添花,耐人尋味,潛移默化
教育需要呈現(xiàn)大量的事實(shí)和論證,思想品德課教學(xué)更是如此,其進(jìn)行的依據(jù)無外乎以下幾種:邏輯推理、事實(shí)論證、數(shù)理分析……筆者認(rèn)為古代詩(shī)詞中蘊(yùn)涵很多這樣的論證方法。思想品德課教學(xué)中以古代詩(shī)詞點(diǎn)綴所起到的效果可以概括為:錦上添花,耐人尋味,潛移默化。比如:在講哀愁的情緒時(shí)可以引用陸游的詞,“無意苦爭(zhēng)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塵”等。總而言之,沒有古代詩(shī)詞點(diǎn)綴的思想品德課教學(xué)可能是淺顯的,但有了古代詩(shī)詞點(diǎn)綴的思想品德課教學(xué)一定是耐人尋味的,給學(xué)生的不是一味的灌輸,而是起到了潛移默化的作用。這樣可以使思想品德課堂富有生機(jī),學(xué)生對(duì)于思想品德這門學(xué)科的興趣就會(huì)油然而生。
三、 以“知”入“行”,由“淺”入“深”,是古代詩(shī)詞和思想品德課教學(xué)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相映成趣的過程
1、是因?yàn)榉蓷l文規(guī)定如此,也就是說,不僅是女犯人,在被斬首時(shí)需要脫了上衣,男犯人也是同樣的。斬首時(shí)脫衣服,一是為了方便,二是為了驗(yàn)證犯人,并沒有特殊針對(duì)女性。
2、因?yàn)橐恍┏舐呐f觀念。有觀點(diǎn)稱,斬首的時(shí)候,女性可以向行刑者申請(qǐng)不用脫衣。因?yàn)榍迥┡⑿矍镨行痰臅r(shí)候,就是穿著衣服的。但是,穿著衣服行刑的另一個(gè)極端,就是女犯人在被砍頭時(shí),會(huì)被扒掉全身的衣服,這是對(duì)犯人的一種羞辱。
3、在平常的電視劇之中,如果是皇親國(guó)戚的犯了重罪,需要被殺死,那么往往是賜給白綾或者是毒藥。這樣,也可以保證這些地位尊崇的人免受羞辱。
4、因?yàn)榕釉诠糯牡匚皇值拖隆K砸话闱闆r下,女子犯罪被判刑,比男子更重。有一個(gè)典型的謀殺親夫案例,犯罪人女的被判死罪,而男的僅僅判為流放。
(來源:文章屋網(wǎng) )
關(guān)鍵詞 《唐律疏議》 司法檢驗(yàn) 制度
中圖分類號(hào):D9297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中國(guó)古代的司法體系是一個(gè)以刑法為主要內(nèi)容的法制體系。刑法條例內(nèi)容多涉及人命損傷及死亡,我國(guó)古代法律條文的詳細(xì)程度必然有完善的檢驗(yàn)經(jīng)驗(yàn)來支持。否則,頒行全國(guó)的律法是無法令人信服的。唐代作為我國(guó)古代的鼎盛朝代未有完整的司法檢驗(yàn)的專著留下。但是,《唐律疏議》的條文中反映了唐代司法檢驗(yàn)制度的一些內(nèi)容。
一、從《唐律疏議》中的定刑看唐代司法檢驗(yàn)
(一)依傷勢(shì)程度定刑罰等級(jí)。
傷及拔發(fā)方寸以上,杖八十。若血從耳目出及內(nèi)損吐血者,各加二等。
諸斗毆人,折齒,毀缺耳鼻,眇一目及折手足指,若破骨及湯火傷人者,徒一年;折二齒、二指以上及髠發(fā)者,徒一年半。
諸斗毆折跌人支體及瞎其一目者,徒三年;即損二事以上,及因歸患令至篤疾,若斷舌及毀敗人險(xiǎn)陰者,流三千里。豍
以上條文出自《唐律疏議》,我們可以明顯的看出不同的傷勢(shì)程度有各個(gè)輕重不同的判刑,但是這里就出現(xiàn)一個(gè)問題,那就是怎么對(duì)這些傷勢(shì)等級(jí)進(jìn)行評(píng)定呢?唐代文獻(xiàn)中少有關(guān)于檢驗(yàn)程序的記載,但是就這些條文的詳細(xì)分類來看,在條文的背后必然有一個(gè)確定傷勢(shì)等級(jí)的過程,至少至唐以來關(guān)于這個(gè)問題已經(jīng)在各種司法實(shí)例中積累了比較豐富的經(jīng)驗(yàn)。
(二) 依傷人原因定刑。
諸斗毆人者,笞四十;傷及以他物毆人者,杖六十;
諸斗以兵刃斫射人,不著者,杖一百。若刃傷,及折人肋、眇其兩目,墮人胎,徒二年。
諸斗毆?dú)⑷苏撸g。以刃及故殺人者,斬。雖因斗,而用兵刃殺者,與故殺同。豎
這些條文中把致傷原因分為了:手足、他物和兵刃。根據(jù)《唐律疏議》中的解釋:手足是指用人身上的身體部位擊傷別人;他物是指除手足和兵刃之外的其他物品傷人;兵刃是指用金屬器物傷人或傷人。相較而定,使用兵刃傷人或殺人判刑是要比較重,在后世的司法檢驗(yàn)記載中也沿用了這種分類方式。
二、《唐律疏議》中的其他檢驗(yàn)制度
(一)檢驗(yàn)稱詐的處理。
諸有詐病及死傷,受檢驗(yàn)不實(shí)者,各依所欺,減一等。若實(shí)病死及傷,不以實(shí)驗(yàn)者,以故入人罪論。
《唐律疏議》中這段話明確的講明了唐代存在司法檢驗(yàn)程序,如果在司法實(shí)踐遇到有人“詐病”或是“死傷”,政府會(huì)派遣人員去檢驗(yàn)實(shí)際情況。此條律中明顯表現(xiàn)出兩個(gè)方面的懲罰情況:一方面,受檢驗(yàn)者如果有不實(shí)之處要受到懲罰;另一方面,檢驗(yàn)者如果沒有據(jù)實(shí)檢驗(yàn)也要入罪制裁。也就是說,唐代不僅存在司法檢驗(yàn)制度,而且應(yīng)該有相應(yīng)的監(jiān)督制度來保證檢驗(yàn)中不出現(xiàn)舞弊現(xiàn)象。
(二)《唐律疏議》中的文書檢驗(yàn)。
諸詐為官文書及增減者,杖一百;準(zhǔn)所規(guī)避,徒罪以上,各加本罪二等;未施行,各減一等。
【疏】議曰:“詐為官文書”,謂詐為文案及符、移、解牒、鈔券之類,或增減以動(dòng)事者,杖一百。準(zhǔn)所規(guī)避之事,當(dāng)徒罪以上,事發(fā)者,各加本罪二等;未發(fā),即依二罪之法,從重科之。規(guī)避者,假有於法不應(yīng)為官,詐求得官者,徒二年;又詐為官文書及增減而規(guī)官不解,加本罪二等,合徒三年。避者,或有本犯徒三年,詐為增減以避此罪者,合加二等,流二千五百里。即詐為官文書及增減訖,事未施行,“各減一等”,杖罪以下,杖上減;徒罪以上,各從徒、流、死上減。
即主司自有所避,違式造立及增減文案,杖罪以下,杖一百;徒罪以上,各加所避罪一等;(造立即坐。)若增減以避稽者,杖八十。
從此條律中,我們可以知曉:一方面,關(guān)于日常政府各類文書的制作和使用有比較嚴(yán)格的規(guī)定,若是在行政過程中發(fā)現(xiàn)假文書懲罰比較嚴(yán)重;另一方面,在唐代,文書的使用有嚴(yán)格的程序,在文書的使用過程中接收文書的人要有辨別文書的真?zhèn)蔚哪芰Γ駝t在行使職權(quán)過程中就會(huì)出現(xiàn)差錯(cuò)。
三、《唐律疏議》中保辜制度的檢驗(yàn)
保辜制度的基本內(nèi)容是指?jìng)ψ镌趥槲炊〞r(shí),由犯罪人保養(yǎng)被害人的傷情使人及早平復(fù),以減免犯罪者罪責(zé)的制度。《唐律疏議·斗訟》中有以下條文:
諸斗毆折跌人支體及瞎其一目者,徒三年;辜內(nèi)平復(fù)者各減二等。
諸保辜者,手足毆傷人者二十日,以刃及湯火傷人者三十日,折跌人支體及破骨者五十日。限內(nèi)死者,各依殺人論,其在限外及雖在限內(nèi),以他故死者,各依本毆傷法。豑
這段話中依據(jù)不同的傷勢(shì)制定了不同的保辜期限,也就是說,有專門的人來視察傷勢(shì)病情,定奪是何種級(jí)別的傷害以確定保辜日期,并作為日后司法制裁的重要憑據(jù)。
《唐律疏議》中雖未給我們展現(xiàn)明確的司法檢驗(yàn)體系,卻告訴我們唐代有這樣一個(gè)體系,同時(shí)不斷地司法實(shí)踐也為宋代產(chǎn)生法醫(yī)學(xué)著作奠定了基礎(chǔ)。
注釋:
【關(guān)鍵詞】傳統(tǒng)司法 禮法 時(shí)宜 【中圖分類號(hào)】D909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日本學(xué)者滋賀秀三曾說,“在中國(guó)古代幾乎找不到與國(guó)家權(quán)力分離而具有獨(dú)立地位的法界精英,從理性的探索中產(chǎn)生學(xué)說,判例,以創(chuàng)造并支持‘法’”。這種對(duì)傳統(tǒng)司法文化的誤讀,完全遮蔽了中國(guó)古代司法兼容并包、因時(shí)而變的文化品格,矮化了司法官獨(dú)立的人格地位。傳統(tǒng)的司法文化既重視天理、國(guó)法、人情的邏輯自洽,在自然法與人法之間尋求巧妙的平衡,又注重自我更新,強(qiáng)調(diào)司法符合社會(huì)的變革與時(shí)代的精神。
“以禮入法”的情理品格
先秦法家認(rèn)為,“一民之軌莫如法”,只要以成文法規(guī)作為國(guó)家治理的工具,那么司法官便可以得心應(yīng)手地運(yùn)用他們對(duì)法典的理解力與內(nèi)在道德判斷力來統(tǒng)治、教化民眾。而中國(guó)古代的儒家則認(rèn)為,如果人們的行為完全被刑法支配而忽視道德倫理這一社會(huì)政治秩序的最高規(guī)范,那么國(guó)家的治理與司法的可信度肯定會(huì)遭到破壞,所謂“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yè)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guó)?”便是這個(gè)道理。
先秦的法家與儒家對(duì)于司法倫理的證成都過于偏激,法家具有濃郁的法律工具主義色彩,且儒家又過分放大了人在司法中的作用,最終容易導(dǎo)致“有治人,而無治法”的局面。因此,為了調(diào)和二者之間的沖突,并盡可能在司法實(shí)踐中充分發(fā)揮天理人情與成文法典的各自優(yōu)勢(shì),取長(zhǎng)補(bǔ)短,在歷史觀念的演進(jìn)中,德主刑輔、禮刑并用逐步成為中國(guó)傳統(tǒng)司法文化的內(nèi)核,“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為表里者也”。這兩者之間的完美結(jié)合,實(shí)際上反映了中華傳統(tǒng)司法文化既秉持公平正義的自然法秩序,又倡導(dǎo)時(shí)代精神、體現(xiàn)人情與民意。
中國(guó)古代的法律文本時(shí)刻提醒司法官,法律是因人而設(shè)置的,所以司法并不是簡(jiǎn)單的案例判決,而是要時(shí)刻因循人性,凸顯人在整個(gè)宇宙秩序中的重要地位。例如,《唐律疏議》開篇即云:“稟氣含靈,人為稱首。莫不憑黎元而樹司宰,因政教而施刑法。”正是因?yàn)橛兄@樣人性化的法理精神,從周代開始便有了“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的審判制度,法官通過觀察人的言行舉止、喜怒哀樂等心理變化來進(jìn)行判斷,這也可以視為是最早的司法心理學(xué)。到了漢代又有了“經(jīng)義決獄”制度,在無成文法規(guī)定的情況下,準(zhǔn)許司法官援引儒家典籍中的記載作為審理案件的依據(jù)。
在司法實(shí)踐中,往往提倡司法官要遵循以禮入法的司法精神,如此才能達(dá)成司法的公平與公正,“故公平者,職之衡也;中和者,聽之繩也。其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類”是人認(rèn)知自然的理性產(chǎn)物,是宇宙萬(wàn)物在人心中的基本準(zhǔn)則,“類”是法律條文的比附,法律條文是“類”的擬制。因此,在禮法合治的傳統(tǒng)中,公平公正、寬嚴(yán)相濟(jì)是司法應(yīng)當(dāng)遵循的根本準(zhǔn)則。在司法適用上,首先考慮的是成文法的公正性與權(quán)威性,因法的本質(zhì)就是人情與自然秩序的成文法;在司法救濟(jì)上,又強(qiáng)調(diào)人情與道德律是對(duì)成文規(guī)則的補(bǔ)充,以此彌補(bǔ)法律道德性的缺失。
“不法常可”的變法品格
在法的穩(wěn)定性與適應(yīng)性之間,在“天理”與“人情”之間,傳統(tǒng)司法官十分注重法律效果與社會(huì)效果的統(tǒng)一,因而,對(duì)人情的包容與法律的變通也直接體現(xiàn)了司法領(lǐng)域的變法思想。在適用條文之外,執(zhí)法者有時(shí)候能跳出成文法的約束,善于運(yùn)用經(jīng)年累月的道德準(zhǔn)則進(jìn)行曲直是非的判斷;在司法實(shí)務(wù)中,既關(guān)注法典判例,又能回歸現(xiàn)實(shí)問題,強(qiáng)調(diào)實(shí)行、實(shí)際與使用。
只有@樣,傳統(tǒng)的立法與司法體系才會(huì)不斷地自我更新,可以說整個(gè)中國(guó)上下五千年的司法經(jīng)驗(yàn)與教訓(xùn),本質(zhì)上就是一部在不斷試錯(cuò)、不斷成長(zhǎng)的變法史。馬克思曾指出,“法律必須以社會(huì)為基礎(chǔ)”,社會(huì)的變遷是法律發(fā)展的根本前提。實(shí)際上中國(guó)古人已經(jīng)早有這樣的認(rèn)知,比如,商君曾說,“湯武之王也,不循古而興;殷夏之滅也,不易禮而亡”、“茍可以強(qiáng)國(guó),不法其故;茍可以利民,不循其禮”,變法是實(shí)現(xiàn)國(guó)家富強(qiáng)的根本前提,而國(guó)家治理與法律適用的方式也并不是絕對(duì)刻板的;韓子的“不期修古,不法常可”,指出了不必盡遵古制與常規(guī),而是要根據(jù)具體情況研究社會(huì)實(shí)際情況,制定相應(yīng)措施;北宋年間王安石的“所遭之變,所遇之勢(shì),亦各不同,其施設(shè)之方亦皆殊”,這與韓子的變法思想可謂一脈相承;蘇轍的“任人不若任勢(shì),而變吏不若變法”,既取決于立法者能否用于揚(yáng)棄舊制,更定新法,還在于司法者能否“度務(wù)而制事”,在變動(dòng)不居的社會(huì)情勢(shì)與可能漸趨僵硬的“祖宗成法”之間合理運(yùn)用變法的精神,在規(guī)則與道德之間靈活變通。
變法的本質(zhì)是改革,變法的形式是立法。從管仲、李悝、商鞅一直到王安石、張居正,這些被寫入變法史冊(cè)的改革家理所當(dāng)然是中國(guó)歷史上偉大的立法者和法理學(xué)大師。但是,也要看到,中國(guó)歷史上一次又一次的變法經(jīng)驗(yàn),無不是從具體的司法實(shí)踐中總結(jié)出來的。比如,盡管中國(guó)古代總體上還是強(qiáng)調(diào)“先王之法不可變”,但儒家同時(shí)也主張應(yīng)以動(dòng)機(jī)和目的的善惡而非絕對(duì)的法律條文來定刑論罪,“志善而違于法者免,志惡而合于法者誅”,如果犯罪動(dòng)機(jī)符合公序良俗,那么即便這種行為觸犯了法律,也可以據(jù)自然法準(zhǔn)則減輕或免除處罰。所以,中國(guó)司法史上出現(xiàn)的“原情定罪”、“曲法”、“慮囚”等制度,并非是過去人們所說的人治的產(chǎn)物,而更多的應(yīng)視為是古人司法智慧的結(jié)晶。正如民國(guó)時(shí)期的法學(xué)家吳經(jīng)熊所說,“法學(xué)的進(jìn)化并不是循著一條直線。進(jìn)化的路程似乎是一條曲線――一條螺旋式的曲線。法學(xué)是趨重于情感的,以‘變’為前提的”。古人的高明之處在于,如果法律的精神不能與社會(huì)、與人倫相為融合、變通,那么法條不過就是“具文”,甚至可以棄之不用,而要做到人法合一,必須在制定、修改、適用法律之際,具備變通的思維。縱觀中國(guó)古代任何一次變法所依循的原理與倡導(dǎo)的精神,無不濫觴于此。
“法與時(shí)轉(zhuǎn)”的時(shí)代品格
法律除了要符合天理人情、符合社會(huì)的變革,更要彰顯時(shí)代的精神。“法學(xué)不過是思想的一個(gè)支流,當(dāng)然免不了受那風(fēng)行的人生觀和科學(xué)思想的影響。思想是不脛而走的;思想是無孔不入的。法學(xué)是無時(shí)不在時(shí)代思想浸之中。”每一個(gè)時(shí)代有每個(gè)時(shí)代“變”與“不變”的價(jià)值,懂得在這二者之間進(jìn)行甄別與取舍,司法者便能具有時(shí)代觀。譬如,“法宜其時(shí)則治”、“法不當(dāng)時(shí),而務(wù)不適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禮法以時(shí)而定,制令各順其宜”。
“因時(shí)”是傳統(tǒng)司法彰顯其生命力的根本所在。《禮記?月令》曾說,“仲春之月,毋肆掠,止獄訟”。又如《春秋繁露》所言“天有四時(shí),王有四政,慶、賞、刑、罰與春、夏、秋、冬以類相應(yīng)。”春天是萬(wàn)物復(fù)蘇生長(zhǎng)的季節(jié),因此,刑殺不可以與天意相違背,而秋冬是萬(wàn)物肅殺的季節(jié),刑罰正宜其時(shí)。由此可見,社會(huì)的變革與時(shí)代的訴求造就了中華傳統(tǒng)司法包容、開放的性格,傳統(tǒng)的司法不僅注重吸收各個(gè)朝代的法律變革的智慧,更注重借鑒各個(gè)民族的法律傳統(tǒng)。法律并非萬(wàn)能,法律的執(zhí)行離不開人;法律不能調(diào)整人的所有事項(xiàng);法律也不可能預(yù)見每一個(gè)時(shí)代的特性,因而,到了近代,更是強(qiáng)調(diào)要建立中華本位的司法文化。時(shí)代的理想昭示著法律的實(shí)施必須體現(xiàn)近代法治的精神,而司法的時(shí)代性也是法治的一個(gè)重要特征,所謂“法與時(shí)轉(zhuǎn)則治,治與時(shí)宜則有功”便是這個(gè)道理。法律的實(shí)施是檢驗(yàn)時(shí)代性的一個(gè)重要指標(biāo),民國(guó)時(shí)期法學(xué)家梅仲協(xié)曾說,“法官的任務(wù),不僅在適用法律,得其平允,于解釋法律,尤須符合時(shí)代精神”。一個(gè)國(guó)家的司法制度,最重要的條件就是要顧及人民的實(shí)際生活,適應(yīng)時(shí)代的人群需要,不背國(guó)情,不違潮流。
(作者單位:美國(guó)埃默里大學(xué)法學(xué)院)
【參考文獻(xiàn)】

預(yù)計(jì)1個(gè)月內(nèi)審稿 省級(jí)期刊
芝加哥大學(xué)東亞藝術(shù)研究中心;中央美術(shù)學(xué)院人文學(xué)院;北京大學(xué)視覺與圖像研究中心主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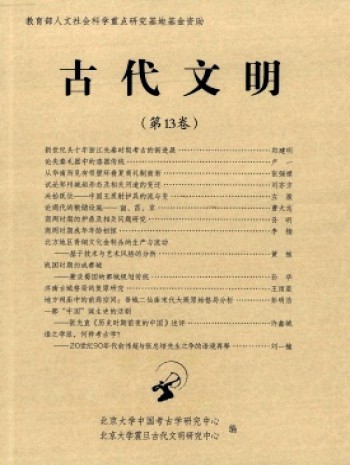
預(yù)計(jì)1個(gè)月內(nèi)審稿 省級(jí)期刊
北京大學(xué)中國(guó)考古學(xué)研究中心主辦

預(yù)計(jì)1-3個(gè)月審稿 CSSCI南大期刊
東北師范大學(xué)主辦

預(yù)計(jì)1個(gè)月內(nèi)審稿 省級(jí)期刊
蘭州城市學(xué)院中國(guó)古代小說戲劇研究所主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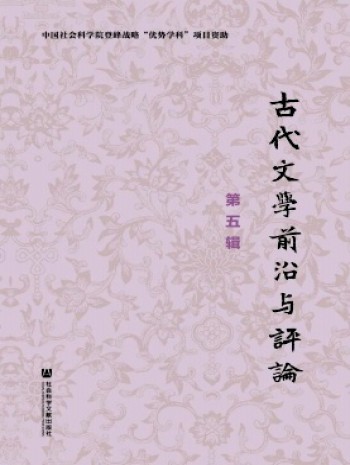
預(yù)計(jì)1個(gè)月內(nèi)審稿 部級(jí)期刊
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院文學(xué)研究所古代文學(xué)學(xué)科主辦

預(yù)計(jì)1個(gè)月內(nèi)審稿 部級(jí)期刊
中國(guó)政法大學(xué)法律整理研究所主辦